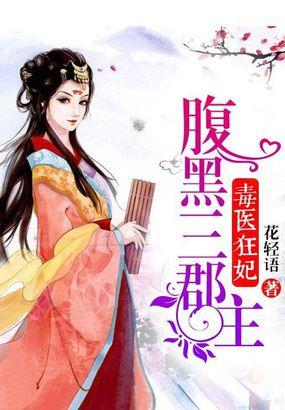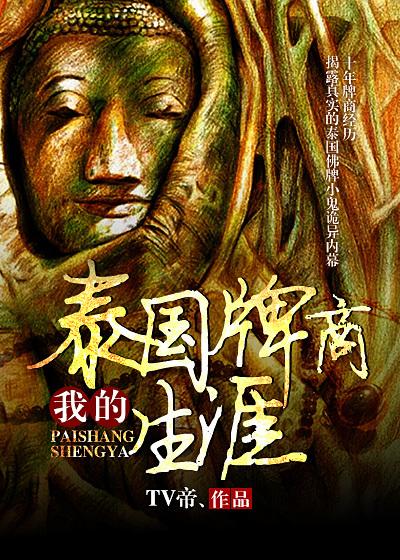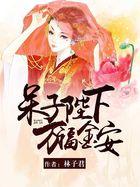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明臣王琼观后感 > 第325章(第1页)
第325章(第1页)
&ldo;奴婢见过张侍读。&rdo;虽然已经是清宁宫的主事太监了,但是在张信面前崔文可不敢露出趾高气扬的派头来,反而小心翼翼堆起满面笑容。
&ldo;用不着这么客气,坐下来说话。&rdo;张信微笑起来,心情舒畅的时候看什么都顺眼,崔文当然是十分乐意地坐下。
&ldo;张侍读,娘娘有旨,召见绿绮姑娘。&rdo;喝了口仆役端上来地热茶之后,感觉身上的寒气消去许多,崔文这才表明自己地来意,如是不是为了讨好蒋后,他才不会离开温暖如春的皇宫,跑来宫外来受这个罪呢。
&ldo;娘娘有什么事情吗?&rdo;张信皱眉问道,好心情马上随着这个消息散去了,蒋后该不会是后悔了吧,肯定要询问清楚,不然等会自己与绿绮两人进宫。却是自己一个人回来,那可就欲哭无泪啊。
&ldo;娘娘这是在思念绿绮姑娘呢。&rdo;崔文解释说道,就凭着这点,自己就应该亲自来跑一躺,好给娘娘留下好印象啊。
&ldo;恰好我也有事进宫面圣,我们一同前去吧。&rdo;张信当然不敢违抗蒋后的旨意,思考片刻之后还是不放心,干脆也跟着去,如果蒋后到时不放人的话,也好找皇帝说理啊。反正事情与自己无关,崔文当然不会有意见。
&ldo;你在这里稍等,我去和绿绮说,让她准备一下。&rdo;张信点头说道。
&ldo;好的,张侍读请。&rdo;崔文笑道,却发现张信没有急着离开之意。不由莫明其妙的看着他,询问起来:&ldo;张侍读还有什么事情吗?&rdo;
&ldo;崔文,待会见到绿绮地时候,你怎么称呼她。&rdo;张信淡淡问道,总是姑娘长姑娘短的叫唤,分明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ldo;当然是。张夫人啦。&rdo;像崔文机灵的人,当然不用刻意提醒,他自己看出张信脸上不悦之色,稍微思考片刻,马上清楚错误之处,不由立即纠正起来。
&ldo;明白就好。&rdo;张信笑了起来,转身走了,留下哭笑不得的崔文。
当张信把蒋后的意思告诉绿绮之后,她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反而露出开心的笑容。这让张信非常无奈,细心的为绿绮换上狐绒毛衣之后,张信就带着绿绮出发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崔文称呼自己为张夫人之后,绿绮那灿烂的笑容十分光彩照人,连不近女色的崔文都为之一滞,更加不说用府中地仆役啦。
虽然说张信以前进宫都习惯步行,但是为了不让绿绮受累,自然是准备好轿子,当轿子起行之后,自己骑着马跟随旁边,抵达皇城的时候当然要经过搜查。不过搜查绿绮的时候自然会由宫里的女官负责的。
等到了乾清门时。没有皇帝的旨意,张信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绿绮被几个宫女太监给领走了。不久之后在清宁宫内殿之中,蒋后挥去左右接着绿绮的小手询问起来,从绿绮通红的脸蛋上可以知道这些问题应该非常私隐,隐隐约约似乎有什么传授、秘术之类的词汇。
&ldo;张侍读,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和朕说,为何在这里左顾右盼的。&rdo;看到坐立不安的张信,朱厚感到非常好笑,没有想到在人前一向镇定自若地张信,居然会担心绿绮姐姐被母后抢占过去。
&ldo;启禀皇上,这段时间来,臣已经将东厂整合一遍,这是各个官署总旗以上官员的名单,请皇上过目。&rdo;既然敢进宫,张信自然会有借口。
正如郭勋猜测的那样,早在张信整治内帑的时候,朱厚已经把东厂交给张信管理,虽然对太监反感,但是朱厚还是明白东厂对自己维持统治是有帮助的,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东厂,但是亲自掌管东厂一段时间之后,朱厚马上被东厂那些繁琐杂乱无章的情报给弄晕了,况且自己还要处理朝政,自然没有多少时间处理东厂的事情,经过考虑之后,朱厚自然而然的想到张信。
而张信对这样的任务还是有几分兴趣的,屏弃东厂地名声不说,它怎么说也是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情报机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的国家情报机构,这么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亮出身份来,况且情报意味着什么,张信自然清楚明白。
经过蒋冕和朱厚的梳理,东厂真可谓损失惨重,对张信的接任自然不会反对,而且有几分欢迎之意,都知道张信是皇帝的亲信,由他管理东厂,那说明皇帝还没有放弃东厂,不会像西厂和内行厂一样被撤销啦。
所以张信根本不用怎么恩威并施,就顺理成章的彻底执掌在自己手下,当接手之后张信才发现,东厂没有世人想象中的那么神通广大,什么京城哪个官员说的某句话,第二天就会摆在皇帝龙案面前,那根本是无稽之谈。
经过询问之后张信才明白,原来这是东厂与锦衣卫自己放出的风声,为的就是让世人害怕自己,使劲的把两个机构地能力无限夸大,再把一些事情经过加工处理,其实有很多事情他们根本查不出来地,张信对此也深以为然,毕竟古代没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哪里有这个本事能监听别人地言行举止啊。
正文1
第一百五十一章波澜
锦衣卫与东厂情报准确的故事在民间可是大名鼎鼎的,而其中又以发生在明初的开国功臣宋濂身上的故事最有名,事情世人皆知,话说有一天晚上,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自然要招待客人,陪其饮酒,次日上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他当时的情况,宋濂一一作了如实回答,等宋濂回答完毕,朱元璋哈哈大笑,夸赞宋濂诚实,还把一幅画拿出来给他看,却是宋濂家待客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