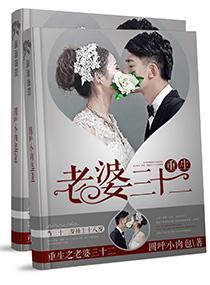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曾经风华今眇然好看吗 > 第145章(第1页)
第145章(第1页)
三四天的工夫,雪已经化了不少,院中和窗台上的雪人都更丑了,但祁襄和白君瑜都不舍得让人收拾了,就那么放着。
趁着阳光好,祁襄坐在窗边串奉北将军的铠甲,有了上回的经验,他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纤细白皙的脖颈低出一个很美的角度,让白君瑜想凑过去与他厮磨,也不禁想起祁襄后仰到极致的迷人弧度,甚至肩头的粉红和炙热的呼吸都像在眼前,撩人心弦。
扯走他手上的铠甲,白君瑜抱住他,自己向后躺下,让祁襄伏于他身上。
祁襄纵容地拿过他刚才在看的书,随意扫了几眼,“不好看?”
“不好看。”白君瑜笃定道:“没有你好看。也……想你了。”
祁襄拿书拍他肩膀,“青天白日的,乱想什么?”
他太明白白君瑜的“想你”是指什么了,只是朗朗白日,他可不成。
“怎么就是乱想,想你才是正常。”他的古板在与祁襄两情相悦后,似乎被丢的一点不剩了。祁襄反而显得保守起来,别说白日做些什么,就连不熄烛火都会僵硬好一阵。
祁襄爬起来,“你若无事可做,就去军中比划一番,消耗些力气。”
白君瑜嗤笑,“我有软榻,有暖屋,还有你,尽有可消耗的地方,为何要顶着寒气去军营。”
“你不要脸我还要的。”祁襄再喜欢也还是要脸的,这并不冲突。
“之前在我那儿看到画本,脸不红心不跳的是你,怎么如今矜持守旧的还是你。”白君瑜喜欢祁襄从保守到忘情的样子,那都是他给祁襄的,也是他的得意。
祁襄不欲与他靠太近,赶紧给自己换了个位置,“当初恪守礼度的是你,现在变着法的什么都想试的也是你,难道不是应该你反省吗?”
“反省?我只恨春宵苦短。等哪日我辞了官,就可以整日陪你了。”白君瑜觉得那才是神仙日子,不负此生。
你还是继续当官吧——祁襄心道。
见祁襄实在没有那个意思,白君瑜也不勉强,“
和你说点正事,今天上朝时,四皇子同我说,大皇子和皇后的人都已经盯住玉栀宫了。那枚扳指娇昭仪自己收了起来。可能以为是二皇子出门祈福前到她宫中小坐时落在她那里的,今天刚发现而已。”
祁襄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就怕动了真感情。遇到个良人也罢了,就是这种明明身倚危险,却抱有侥幸,沉溺不肯清醒,最后刀架脖子上了才明白过来的人,才最可悲。”
“那我算良人吗?”白君瑜真是很喜欢把这种话题往自己身上拉。
祁襄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只能闭着眼睛夸,“算,我只认你一个。”
白君瑜满意了,又压低了声音说道:“如果二皇子跟娇昭仪真有什么,那娇昭仪的孩子……”
祁襄说:“算一算我提议让娇昭仪有孕的日子,如果二皇子之后才打的这种主意,那按时间算孩子不可能是二皇子的。”
“那二皇子倒还有活命的可能。”这事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还得等真相大白的时候方能知晓。
命是能活,但风光必然不在了,祁襄不知道二皇子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对于一个充满野心的人来讲,无论能力高低,被压进土里爬不起来,不得不认命,才是最不能接受的事。
贤珵早了荣清一日回府,荣清本要祈福七日,但提前两天说要多留一日,再诚心祈福一番才能安心。贤珵假惺惺地赞扬了荣清的仁孝,荣清听得舒服,也谦虚了几句。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贤珵是有意引导着荣清认为自己的野心是配得上能力的,只是缺少他人的支持,所以显得无用。就像三皇子,本也不出挑,就因为背后的势力大,所以皇上之前也要重用,别人自然觉得三皇子是很有能力的人。加上荣清本就对皇上的态度不满,就信以为真的,一副引贤珵为知己的样子。贤珵提醒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在宫中的地位,而要稳固地位,就要抓紧手上现有的人脉,再徐徐图之,缓缓扩张。
荣清这几日也被贤珵口若悬河说得激情澎湃,也觉得是佛门之地清静,让他能想明白更多事情,更以此为自己的福地,有了别的打算。
贤珵依依不舍地与荣清道别,相约日后再聚,场面一度可以作诗一首。
娇昭仪伪装成宫女,前脚刚出宫门,后脚就有大皇子的人跟了上去。皇后得到消息后,兴奋得脸都红了,赶紧让自己的人也跟上,自己随后就到。
今日是近来难得的暖和天,上山参拜的香客非常多,娇昭仪混在人群里,还真没有人特别注意她。
进了寺中,绕去后山,荣清的小厮已经等在那里了。见无人跟踪,才扶着娇昭仪来到荣清所住的院子。
娇昭仪迫不及待地进了屋,期期艾艾地喊着“二郎”。
荣清见到娇昭仪也是一阵欣喜,两个人便搂在了一处。
“二郎轻减了不少,可是寺中生活太辛苦了?”这样简陋的条件,若是她,肯定一天也住不下去。
荣清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说:“不辛苦,为你祈福怎么会辛苦?”
娇昭仪笑颜如花,“我这几日可是惦记着二郎呢。这山中我的宫女不宜常来,也没有你的消息,我一个人在宫中真的闷坏了。”
荣清安慰着她:“你且忍忍,等以后到了我们的好日子,你想去哪儿,我都陪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