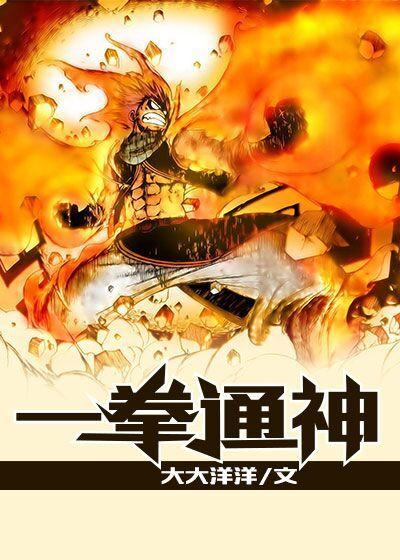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沃辛传奇 豆瓣 > 第129章(第1页)
第129章(第1页)
林克瑞将孩子重又放了回去。连你的家人都不要你,我这个陌生人也不要你,他心想。孩子哭得声嘶力竭。死吧,孩子,早点解脱,林克瑞心想。&ldo;我帮不了你。&rdo;他大声说。
&ldo;说什么呢,你画得那么好?&rdo;扎德不解地问。但林克瑞心知肚明。他原打算画扎德,却画成了妈妈。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回避了七个月的事实‐‐扎德像他妈妈。所以那一晚他才穿街走巷,两眼不离地跟着她,直到她忍不住问,&ldo;你到底‐‐&rdo;
&ldo;我到底什么?&rdo;扎德问。但林克瑞没有作声,只是笨手笨脚地将画揉作一团(你真笨,林克瑞!),按在大腿上,打了这张纸,也是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下。他疼得喊了一声,接着又捶了一下。
&ldo;喂!喂,住手!别‐‐&rdo;
接着他看到,感到,闻到,听到,妈妈俯下身,头发拂过他的脸庞(香喷喷的头发)。林克瑞顿时又充满无奈的怒火,一段段清晰的记忆让他无可奈何。在这首都的贫民区,政府提供的一套摆满了画的公寓里,他与这个女人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亲热。我是个大人了,他心想,我比她强壮。可她还想处处管着我,还想打我,对我寄予厚望,而我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于是他不再打自己,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
孩子依然哭个不停。林克瑞手足无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发抖。一阵风让他想起,今夜自己要赎却罪孽,死在这片荒原上。他希望孩子被小虫吸干血,被夜里出没的野兽咬死,被风冻死。当然,区别在于,婴儿不懂,也绝不会懂,他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还不如没有记忆,还不如没有疼痛。
林克瑞伸手掐住婴儿的脖子。不如现在就杀了他,免得半夜再多受罪。可正当他要用力,了断他的血流和呼吸时,林克瑞发现自己下不了手。
&ldo;我不是杀手。&rdo;林克瑞说,&ldo;我帮不了你。&rdo;
他站起身,丢下啼哭的孩子走了,拂动草丛的风声淹没了孩子的啼哭。叶片划着他裸露的胸膛,他记起妈妈给他搓澡。&ldo;看到了没?只有妈妈才能够到你的背,你离不开我。别给我弄脏了。&rdo;
我离不开你。
&ldo;这才是妈妈的乖孩子。&rdo;
是的,我是,我是乖孩子。
&ldo;别碰我,我不许任何男人碰我!&rdo;
但你说‐‐
&ldo;我受够了男人。你这个杂种,老杂种生的小杂种,害得我都老了!&rdo;
可是妈妈‐‐
&ldo;不,不,天哪,我都干了什么呀?男人那样不是你的错。你可不一样,你,我可爱的小宝贝,给妈妈一个拥抱‐‐太紧了,哎呀,你个讨厌鬼,你想干吗?回你的房间去!&rdo;
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跌跌撞撞,摔了一跤,草割破了他的手腕。
&ldo;你为什么打我?&rdo;他听着那个本应是金发的褐发女人喊道。他又打了她一拳,她逃出了公寓,冲向楼梯,跌跌撞撞地冲上了大街。他抓住跌跌撞撞的她,在大马路上掐得她失声尖叫。他要让她知道男人的真面目,然后将她一把扔得远远的。
一把尖刀插进了他的胸膛。
他从草丛中抬起头,只见一个短小粗壮的人。不,不是人,是一个瓦克;也不是一个,是六七个,全副武装,尽管刚从地上爬起来,还睡眼蒙眬。他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一个瓦克的宿营地。
总好过虫子和野兽,他心想。一股凶险和寒冷袭上他的脊梁,他两腿发软,等着这一刀。
但刀却没扎到他的心脏,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刚好就是那个戕害瓦克的男人的继承人,不是吗?他的重型拖拉机把十几个部落的房屋和庄稼夷为平地,他的猎手杀光了流浪到他的地盘上的瓦克。我拥有半颗潘帕斯星球,我是半个值得拥有的世界的主人;杀了我,你们就能重返家园了。
一个瓦克气急败坏地说了句什么。林克瑞估计他说的是扎进去,所以也不耐烦地吼了一句。动手吧,痛快些。
出人意料的是,那个瓦克非但没有回应他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反而退后一步;但他仍拿刀指着林克瑞。瓦克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夹杂着许多颤舌音r和拖长音s‐‐不是公立学校教孩子们的人类的语言。林克瑞十分清楚,瓦克语言不过是退化的西班牙语,数十篇人类学公报指出,瓦克显然是人们认为在数千年前的星际移民早期,失踪的移民飞船&ldo;阿根廷号&rdo;的后裔,当时人类刚刚走出那个被他们彻底糟蹋了的小行星。人类,肯定是人类,但无情的潘帕斯导致了他们的丑恶、冷漠、阴险和无情。
不只是野蛮人的专利。
林克瑞伸手轻轻抓住那只拿刀的手,拉回来,刀尖抵住自己的腹部。接着又不耐烦地说了几句。
那个瓦克瞪大了眼睛,扭头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同伴。他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几个人退了回去,显然是吓坏了。林克瑞不懂。他抓着刀,扎进自己的皮肉;血顺着刀面淌了出来。
瓦克猛地抽出刀,满眼泪水地跪倒在地,抓住林克瑞的手。
林克瑞要推开他的手。谁料这个瓦克跟着他,一点都不反抗。另外几个也围拢过来,他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看懂了他们的姿势。他们崇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