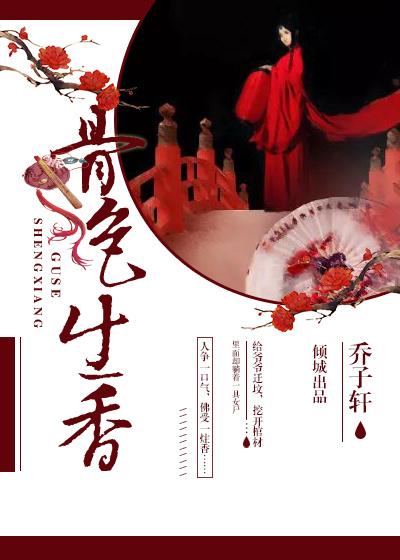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战士3美剧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此后,我开始留意街头的音像店。只要里面有带科本头像的磁带,或者是磁带封面设计得比较奇怪,我都会把它们买下。反反复复地听,一遍又一遍。渐渐地,我学会了&ldo;扒带&rdo;。任何一首歌只要听上三遍,我就可以把乐曲的吉他和弦扒下来自己弹唱了。同时,我还学会了创造和弦、学会跟着和弦走向哼几句旋律、学会把自己在课堂上写的胡言乱语套进旋律。于是,一首又一首版权归我所有的原创歌曲就产生了。
当然,我不会忘记在歌唱间隙像科本一样嘟囔出&ldo;shit&rdo;或者&ldo;fuckyou&rdo;,还像科本一样穿起带斑马条纹的&ldo;海魂衫&rdo;,牛仔裤上也割出了破洞。但我却没有像科本那样在一首歌唱完之后把手里的木琴愤怒地摔在地上,摔个粉碎。尽管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摔琴欲望。那时候如果你敢答应说给我买把新琴,我想我当场就会摔给你看。我的变化令爸爸妈妈感到了伤心。屡次劝说无效,他们就懒得理我了。孤独随之袭来。
第一部分寻找有相同爱好的伙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了摆脱孤独,我开始寻找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伙伴。有人满脸神秘地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某某地方有好几拨。某某地方是我们这座城市里惟一一家专卖&ldo;打口磁带&rdo;的商店。出入这家商店的青年大都与我的年纪相差无几。不但年龄相仿,而且我们所崇拜与恶心的人物还就是那么几个。更为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写歌。不同的是,他们个个都长发飘逸。我得承认,他们的弹琴技艺的确比我高明,而且写出的歌曲也比我的更动听。我怀疑这与头发的长短有关,很想像他们一样留起长发。考虑到老爷子那条阴柔险峻的皮带,我只好压制了留长发的欲望,一压就是好几年。
高二那年,我实在压不住留长发的欲望了。心甘情愿承受老爷子几次皮带之苦过后,我买了剃须刀片,一天到晚都拿在手上,后来干脆用透明胶粘在手腕,终于如愿以偿地留起长发。我的长发刚开始飘逸,老爷子的笑脸就不见了。起初我还厚着脸皮向他解释,说古代的中国男人还扎辫子呢,后来连解释我都懒得了。因为老爷子不但不听,而且还骂我狗屁不懂。
既然都这样了,我就尽量避免在家里出现吧。免得惹他伤心,也算是尽了点儿力所能及的孝道。
学校里,愿意与我交好的女生越来越多。我想这与头发长短的关系不大,尽管女生们总喜欢把她们束头发的橡皮筋慷慨相赠,我知道这是看在音乐的分上。那时候,我写出的几首歌曲已经开始在校园里私下流传了。每次下课铃声敲响,总有人哼着我的歌曲走出教室走进厕所然后走出厕所走进教室。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和弦哼唱的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音乐,或者说,这算是什么风格的音乐。后来我们的化学老师回答了我,并且使用了排比句:你的音乐是火种,燎原之火;福音,希望之声;号角,革命旋律;你的音乐是武器;你们的音乐是匕首;你们的音乐是投枪;你的音乐是目前正从中国地下崛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punk。
化学老师的英语比我好,每个老师的英语都比我好。包括对英语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说英语就是鸟语的教导主任。所以,我无法理解punk的具体含意。觉得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朗朗上口,就点点头向化学老师对我音乐的理解表示感谢了。一次课上,化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那天对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言语间洋溢着无尽歌颂与赞扬。于是&ldo;刘健是个punk&rdo;的说法就在本班同学的传播下,长了翅膀似的于校园内传开了。直到有一天我翻看《英汉辞典》,才发现punk的好几种解释都与音乐无关:
a年轻无知的小伙子;
b腐木,朽木,无用废物;
c撑船者,社会底层的卖苦力者;
d流氓;
e引火物;
…………
我一向看不明白过分复杂的《英汉辞典》,于是就去查阅专门介绍音乐种类的书籍,了解punk的真正含义。书上说:punk是摇滚乐的一个分支,punk把摇滚乐的风格推向了极端。punk的兴起和影响主要在英国。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后,原油价格猛涨,英国汽车工业几乎破产。纺织、煤炭、钢铁工业都陷入困境,国际贸易停滞不前。物价上涨,大量工人失业,年轻一代对此毫无办法。失业救济金、政府奖学金和打零工都不能使青少年高兴起来。他们每晚在电视上看到失业数字和工厂关闭的名单,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青年把对生活的失望转为嚎叫。他们愤怒地批评社会各个方面,用声嘶力竭的喊叫、乖戾的形象和疯狂的舞台行为把愤懑裹在音乐里释放出来。&ldo;滚石&rdo;旗下的一位成员说,在punk中,音乐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想恶心什么人……
我不再为自己的音乐名叫punk而担忧,而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妈的我就这样被人推上了船。说来好笑,我和史迪同志成为朋友,竟然是因为他课间去厕所排泄时唱了一首鲍勃&iddot;迪伦的《上帝在我们这边》。当时我就蹲在他旁边。据我所知,他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国内音像公司从没有正式引进,只有经常购买&ldo;打口磁带&rdo;者才熟悉,看来他也是个地地道道的&ldo;打口青年&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