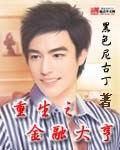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必齐之姜讲的是什么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分房几个月之后,侧夫人容容也怀了身孕。果儿报我这件事的时候,对我还有嗔怪。
我只抚着肚皮,淡淡道了句:&ldo;无妨。&rdo;
&ldo;公主,您倒是大方!&rdo;果儿不依不饶,又顶了我一句。
我笑道:&ldo;你跟了我这么些年,一直护着我,我是知道的。我这作主子的也当关心关心你了,你年纪不小,也该把你许人了。&rdo;
&ldo;果儿陪着公主,不嫁人。&rdo;
&ldo;啊呀,你若不肯,我也没有法子。可是诸儿把阿苏交给我,我总要替他打算,这宫里可有你相好的姊妹,拣个模样好又温顺的,让我许给阿苏。&rdo;
&ldo;哦,我会注意的。&rdo;果儿不看我,闷闷地说。
我戏谑她:&ldo;死丫头,你就硬撑着吧,我就拖到你来求我。&rdo;
果儿哀怨地看我,道:&ldo;公主,您又不愿见阿苏……&rdo;
&ldo;我不见他,又不是不许你嫁他。你只管说你喜不喜欢,我自会给你做主。&rdo;
果儿害羞地点头,一张脸红得像个熟透的桃子。
乘着年节,我就把果儿的婚事办了。她跟了我许多年,在我心里,倒比半夏还亲近几分。如今看她出嫁,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身着喜服的一对新人,金童玉女般站在我面前。这是我来鲁国以后第二次看见阿苏,看见他,果然会想起诸儿。阿苏是诸儿的人,果儿是我的人,这一对璧人站在一处,怎么看都是天作之合。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热衷于媒婆的角色。不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为了能在别人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
果儿的婚礼很简单,他们来拜见我的时候,我给了些赏赐,准了几天假,还在我的宫里替他们办了几桌喜宴。因她是君夫人的贴身侍女,在后宫里多少有些分量,故得了不少馈赠,连几位侧夫人也争相巴结。
容容也在邀请之列,穿了件素色的宽大深衣遮掩住微凸的小腹,怯怯地给我问安。
我和气道:&ldo;姐姐有孕就不必拘礼了,我如今身子沉,不能来扶你,你的辛苦我是知道的。&rdo;我示意她的侍女扶她起来,又关照了几句体己的话。本想叫她在我的身边入席,但不管我表现得多么宽宏大量,也不会松懈这个胆小女人的心防。我不愿给她这样的不自在,就让她坐到别处去了。
我其实并不会害她,我说&ldo;无妨&rdo;,就自有道理。往远处说,鲁国是周公封地,子孙最惜姬旦扶立幼主的圣名。往近处说,姬允本身就是在嫡庶相争,兄弟阋墙中幸存下来的,他在一日,就不会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容容的孩子,即便是个男孩,非嫡非长的,又拿什么来和我的孩子争。
齐姜女子,个个都是后宫典范。不同于姑母的是,我的不骄不妒,源于不爱。
――――――――――――――――――――
次年夏天,热得异乎寻常,好像很久都没有下过雨了。我的产期就在这几日里,所以格外小心,也不再出去乱走,只在院子里的紫藤架下放个漆木榻,斜躺在上面翻翻书简。果儿就在一旁陪着我,替我摇摇扇子。
大暑那天,正看得兴起,只觉竹简上盖过一层阴影,抬头一瞧,原来是天边一团乌云滚滚而来,挡住了光线。我道:&ldo;回屋去吧,要下雨了。&rdo;才一动身子,惊觉一阵腹痛,我捂着肚子,咬牙道:&ldo;果儿,我要生了。&rdo;
我的宫里忙碌起来。我被按在榻上,疼得死去活来。我知道会疼,却不知道是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疼法。
&ldo;果儿,果儿……&rdo;她的手臂被我抓出了血印,我哀叫道:&ldo;是不是天黑了,怎么还没有生出来?&rdo;
&ldo;公主,现在才是晌午,外头是乌云。您再使把力气,很快就好了。&rdo;
稳婆也一个劲地催促我,我被催得心慌意乱,只觉得时间漫长得像凝固了一样,这场灾难仿佛永远也不会过去。我拼命地喊叫着,叫声混合着窗外隆隆的雷鸣,再传进耳朵的时候已经混杂不清。
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我在随即而来的雷鸣声中清晰地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周围有片刻的寂静,我慢慢松懈身体,仿佛得到了救赎。慢慢的,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汗水浸透,就像一个刚被人解救上岸的溺水之人。
&ldo;是个公子。&rdo;稳婆把皱巴巴的孩子抱到我面前,在昏黄的烛火中,我看见了诸儿的眼睛。
&ldo;天黑了?&rdo;我又问。
&ldo;才过未时。&rdo;
&ldo;那是下雨了吧。&rdo;
&ldo;还没有下下来,估计是不会下了。&rdo;
我抿了个笑花,娓娓道:&ldo;我有一个故人,也是生在这种天气,光打雷不下雨。这孩子可别和她一样,也是个别扭的性子。&rdo;
稳婆笑道:&ldo;君夫人有所不知,妾的家乡有个传说,光打雷不下雨也分两种:若是没有闪电,那是上天在发怒;若是雷电齐鸣,就是上天在笑。公子出生的时候,正是天笑,就不知君夫人的故人是哪一种呢?&rdo;
我合上眼睛想了想,轻声道:&ldo;这我倒不清楚了。&rdo;
――――――――――――――――――――
孩子刚满月,姬允就带着我大宴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