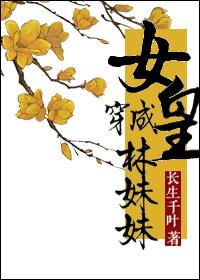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提剑出燕京好看吗 > 第212章(第2页)
第212章(第2页)
热气袭上李蒙的头脸,他整个人僵住,深深吸了一口那勾人口水的香味。一时间仿佛是烟气化作一只扯不断的手,紧紧揪住他的心。
李蒙吸了吸鼻子,馄饨皮入口即化。
永阴永远是这么吵闹,这么充满烟火气,满街都是人,不因夜晚的来临改变分毫。
收工回家的人,左手一包油纸鸡,右手才在街角酒肆沽回的一小坛佳酿或浊酒,美貌的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倚在门前,等待夫郎归家。
吃完馄饨,就在河边一间三层高的酒楼住下,二楼包厢中,阒寂无声。楼下、廊上、两侧屋檐斜斜伸出,掩映的街道上,却人声嘈杂。红男绿女,满街都是流动的热闹。
李蒙喝了几盏酒,就脱了靴,歪在榻上。
这时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
屏风一遮,安巴拉收起笑嘻嘻的脸,轻不可闻地靠到对着河面开的窗户,夜风带来的湿气抚上他的脸,他的浓眉微微颤动着抖开。
巴拉猛然一把抱住他的脖子,糊了他一下巴口水。
安巴拉大笑出声,让巴拉骑到他的脖子上,他望着黑沉沉的天穹,零星的天灯飞向神秘遥远的天意,承载的心愿太沉,令天灯在徐徐微风中也摇摇欲坠。
一道微弱的光辉,从天际坠落。
安巴拉轻不可闻的一声叹息,不带半点痕迹,消散在夜色中。
巴拉睡下后,安巴拉便把他抱到榻上去,打水给他擦手擦脸,之后也靠在榻上,给楼里的小二多五两碎银,这包间就能安静一整晚。
就在安巴拉眼睑止不住下垂,脑袋碰到窗户迷迷糊糊睁眼时,一眼之间,他几乎吓得跳起来。
&ldo;李蒙!你做什么?!&rdo;
李蒙衣袍凌乱,跨骑在窗上,眼神迷蒙地转过来,喃喃自问:&ldo;做什么?&rdo;他的手指快戳到鼻子上去,&ldo;我……&rdo;他打了个嗝儿,楼下人已都散了,河面上泊着三两只画舫,有的点灯,有的已经一片黑暗。
&ldo;我看月亮啊。&rdo;李蒙仰起脖子,眯起眼,&ldo;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呐。&rdo;
安巴拉悄悄靠近他,觑准时机,一把拽住李蒙的胳膊。
李蒙身子一斜,头与肩背俱伸出窗外。
安巴拉直接扑上去一把抱住他的腰,把人拖回来,两人滚在地上,李蒙摔在安巴拉的身上,安巴拉屁股疼得直咧嘴,骂道:&ldo;你不要命了?喝醉了就睡!&rdo;
一股浓烈的酒味刺激得安巴拉直皱鼻子,一手扇了扇。
&ldo;起来,带你去洗澡,洗完再睡,太臭了。&rdo;
李蒙被提着后领子站起,安巴拉才略一松手,就给李蒙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上半身只立住一瞬,就死乞白赖躺在地上,再也不肯起来了。
&ldo;你小子,看着没二两肉,怎么这么沉。&rdo;尝试了两次,抬不动,安巴拉放弃地坐在地上。
李蒙眼睛半闭半睁。
&ldo;睡着了?&rdo;安巴拉的手在李蒙面前一晃,旋即被抓得死死的,拽得安巴拉手都痛。但看李蒙的神情,安巴拉张着一张嘴,平日里插科打诨的那些话,顿时都说不出来。
&ldo;睡吧,睡吧,这世上爱恨嗔痴,睡熟就都忘了。&rdo;
李蒙赫然睁大眼。
他的眼珠黑亮,如同日月星辰置于其中。
安巴拉喉头动了动,嘴一瘪:&ldo;去榻上睡,凉了又要耽误几日,你师父可等不起。&rdo;
李蒙乖顺地点了点头,眼皮又显得困顿非常地耷拉下来。
安巴拉弯腰去扯他,才扶李蒙坐起,一滴,两滴,三滴……接连不断的温热液体落到安巴拉的手上。
李蒙半合了眼,面容沉静,仿佛不知道在哭。
安巴拉暗叫要命,犹豫片刻,抬起手,抚住李蒙的背。
&ldo;别哭了,这么大人了,给你唱歌?&rdo;
李蒙又一巴掌拽住安巴拉的手,这一次用力甚猛,安巴拉手背顿时浮出血痕,哎哟了两声,想挣挣不脱,只怕手骨要被李蒙生生捏碎。
&ldo;你醉了?你醒了?李蒙?你看清楚,你捏的是我的手,我是惹人烦的安巴拉,不是你师父,快撒手。&rdo;那手劲没有再加大,却也没有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