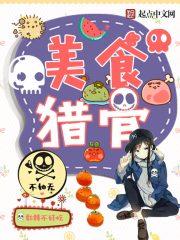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将军夫人娇养手册(重生)TXT > 第107章(第1页)
第107章(第1页)
今晚沈浪醉了,是梨郸的好机会,她不愿意放弃。只要让沈浪上了她的床,一次便可以勾住沈浪一辈子,梨郸有这个信心。
可惜,她不得不放,因为沈浪骤然醒了,他对着金玉说:“阿善,是你啊。”
说着,沈浪自己抬了胳膊,抱住金玉。
梨郸或许没看到,沈浪说这一句话时,眼睛里清亮得很。他压根没醉。
敢作敢当,梨郸并不后悔或者羞愧,她为自己争取了,只是可惜她来晚了,上天没给她一个机会罢了。
沈浪对金玉说话时,那语气十分旖旎。梨郸想,若是有个男子用这样的语气对自己说话,她会一辈子对这个男人好,巴巴用尽手段拴住他的心,不折手段也要得到他。
可惜,沈浪不是她命中注定的男人。
梨郸只是落寞,金玉却是火冒三丈。金玉半夜披了一件单衣出来,本就冷得不行,就为了把沈浪截住。没想到,沈浪从头至尾都是清醒的。
既然沈浪是清醒的,那他为什么要当着梨郸的面假装喝醉了?既然是清醒的,为何要去梨郸的房里?若不是她今晚拦着,沈浪是不是就可以假戏真做了?
呵,男人!
金玉将“醉了”的沈浪架到房里,房里一片乌黑,金玉放了他,便自己上床去睡了。
沈浪轻轻笑了,也不说话,一步步走到床边,慢慢躺下去,压在金玉身上。
金玉还没抱怨,沈浪就开始叫唤了,轻轻“嘶”一声。
金玉咬着嘴唇,不说话,只动了动腰肢,她把沈浪歪下去。她就不该相信他。
沈浪也不挣扎了,他挪到枕头上,看着大开的门外,一地的月光,很明亮:“以为我要假戏真做去梨郸房里?”
“难道不是?”金玉忍无可忍,背地里翻了个白眼。
沈浪挤过来,挨着金玉的背。
黑暗中,金玉像蚯蚓一样,往床里头挪,同沈浪拉开距离。
“我是想看你是不是紧张我。”沈浪又往她背后挤,笑着说,“刚刚看来,你是很紧张我的。”
金玉听到他话语里的得意之情,怒火中烧:“爷,你是一家之主,我们本也说好了,时候到了便和离。若你想要同梨郸圆房,爷自便,不用同我绞尽脑汁想些勉强的借口,这样我也很累。”
金玉再也不想相信他了。说什么出去办正经事,正经事就是带着梨郸出去喝酒亲亲我我么?只有傻子才会一次又一次地相信自己的丈夫出去喝花酒,是因为办正事吧。
只要沈浪挨着自己,金玉就觉得恶心至极,她用肩膀撞开沈浪,咬着牙又往里头挤了挤。
“不相信我?”沈浪问。这些日子以来,金玉从来没有提过“和离”两个字。
沈浪起身坐起来,伸手去掀她的被子。
金玉很烦躁,她压着自己的被子,和沈浪暗中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