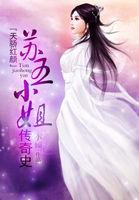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明朝出了个张居正有声在线 > 第117章(第1页)
第117章(第1页)
他在做从长计议了,而且预感不是太好。
当年在归葬的时候,皇帝曾一日三诏飞驰江陵,召他及早回京。这一件盛事,湖广巡按朱琏等地方官始终念念不忘,要为他建造&ldo;三诏亭&rdo;。
他在给朱琏的复信中,发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感慨。他说,修三诏亭,情我领了。但日后世事会有变化,高台倾,湖泊平,我的房子恐怕也不会存在了。这亭子若修起来,到那时也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到什么&ldo;三诏&rdo;!这就是骑虎之势,难以半途而下啊,霍光、宇文护就是这样终不免被祸的!(见《万历野获编》)
霍光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宇文护为西魏大将军、司空,都是主持过皇帝废立的摄政辅臣。霍光死后,祸连家族;宇文护因专权被皇帝所杀。
环顾左右,和者盖寡;仰望君上,天心难测。
张居正是个饱读经典的人,不会不知道&ldo;威权震主&rdo;可能隐伏的危险。史有前鉴,触目惊心!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ldo;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rdo;。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ldo;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rdo;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了,不管前面是陷阱、悬崖还是地雷阵,只能一路走下去。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忘家徇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ldo;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rdo;。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ldo;愤结之日久矣&rdo;(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ldo;工于谋国,拙于谋身&rdo;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ldo;虽有谤言,何足畏哉&rdo;!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ldo;破家沉族&rdo;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ldo;一条鞭法&rdo;。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ldo;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rdo;!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ldo;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rdo;。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ldo;天下晏然如覆盂&rdo;。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