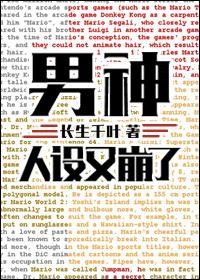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桑道夫伯爵大致内容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ldo;起码,我们还可以写信,收信人能收到吗?&rdo;桑道夫问。
&ldo;我去拿纸、笔、墨水,供你们使用,&rdo;看守回答,&ldo;我只能允诺将你们的信送呈总督。&rdo;
&ldo;谢谢您,我的朋友,&rdo;伯爵说,&ldo;您已倾力而为了!感于您的惠行……&rdo;
&ldo;谢谢就足够了,先生们。&rdo;看守显然很激动。
这个正直的人很快拿来了书写用品。犯人们用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来安排后事。桑道夫伯爵将慈父的爱心,化作千叮万嘱,寄予他即将成为孤儿的小女儿;巴托里在最后的诀别中,明证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扎特马尔则尽情抒发对自己的最后一位朋友‐‐老仆人的真挚情感。
然而,这一天,尽管他们专心致志地书写家信,心情却难以平静。多少次侧耳倾听,期望亲人的脚步声远远响起,穿过主塔楼的走廊;多少次抬首凝眸,像是看见牢门就要敞开,去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这是一种慰藉。可事实上,这道无情的命令,剥夺了他们与亲人诀别的可能,也避免了那令人肝肠寸断的生死离别,反倒更好一点儿。
门没有开。无疑,巴托里夫人和她的儿子,替伯爵抚育小女儿的郎代克,他们都不知道犯人们被捕后关在何处,甚至连鲍立克被禁于特里埃斯特监狱也不知晓。可以肯定,起义领袖被定了什么罪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临刑之前,犯人们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
这一天起初几小时就这么流逝了。时而桑道夫和两位朋友一起聊聊;时而,是长时间的沉寂,他们沉湎于各自的冥想。那时,整个一生在脑中浮现,记忆带着超常的强烈和清晰。并非单纯追溯往昔,唤起的一切回忆同样将观点构筑。难道它们不正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永恒吗?不正预示着一个不可思议、无法估量的无限明天吗?
然而,当巴托里、扎特马尔完全浸于回忆之中时,伯爵却始终被一种顽固的想法所困扰。他坚信在这起神秘的事件中他们被出卖了。以他这种性情的人,若不给予叛徒应有的惩罚,不管叛者是谁,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先死去,他是不肯瞑目的。是谁截获了密码信,使警察借以发现起义,并逮捕了起义领袖?是谁提供了破译密码信的工具?又是谁把它交给、或是出卖给警察局的?面对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伯爵精神亢奋,激动不已。
因此,当他的朋友们安安静静地写信或是一动不动地呆着时,他都如同一头困兽,急躁、不安,沿着牢房的四壁来回走动。
然而就在他完全绝望之际,一种奇特的,但用声学规律又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就要为他揭示出本已认为永远无法破解的秘密。
主塔楼的这一层上,各个牢房的门都开向走廊。有好几次,伯爵从隔墙和走廊的墙壁夹角处走过时,都停了下来。在这个角落,门的接缝处,他确信听到了一种捉摸不定的,相距甚远的喃喃语声。起初,他没有在意;突然,一个人名吐出来‐‐他本人的名字‐‐这令他愈发仔细地凑耳聆听。
显然,一种类似人们在圆顶走廊或椭圆形屋顶的房子里觉察到的声学现象,在这里发生了。声音从椭圆一侧的焦点发出,经拱形面传播开来,能在椭圆另一侧的焦点处听到这声音,中间其他各点都听不到。这就是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宫殿,罗马的圣&iddot;皮埃尔教堂的拱形大厅和伦敦圣&iddot;保罗的&ldo;耳语廊&rdo;中存在的那种声学现象。这些地方,哪怕是低声在拱形建筑的某一焦点上说话,对面也能清楚地听见。
毋需怀疑,有那么二三个人在走廊里或是位于椭圆直径端点之一的牢房里说话,而桑道夫牢房的门正好处在这椭圆形走廊的另一焦点附近。
伯爵做了个手势,两个伙伴便靠近他身边。三个人竖着耳朵,一起在那儿细听。
话音清晰可辨,可一旦谈话人稍微离开焦点,也就是说那决定这种奇特声学现象的一点,句子便断断续续了。
这些就是他们听到的,令他们吃惊不小的只言片语:
&ldo;明天,处决之后,你就自由了……&rdo;
&ldo;那时,桑道夫伯爵的财产,一分为二……&rdo;
&ldo;没有我,或许你还无法破译这封密码信……&rdo;
&ldo;而要不是我,从信鸽脖子上取到信,你根本不会到手……&rdo;
&ldo;总之,没有人会怀疑,全靠我们,警察局才……&rdo;
&ldo;说不准,那些犯人现在正怀疑……&rdo;
&ldo;亲朋、好友,连一个也到不了他们身边……&rdo;
&ldo;明天见,萨卡尼……&rdo;
&ldo;明天见,多龙塔……&rdo;
谈话戛然止住,关门声传了过来。
&ldo;萨卡尼!……西拉斯&iddot;多龙塔……&rdo;伯爵惊叫,&ldo;原来是他们两个!&rdo;
他脸色煞白,望着两位战友。他浑身抽搐,心脏曾一度停止了跳动。瞳孔大得骇人,脖颈僵直,脑袋像要缩进肩膀里去。这一切都表明,这个性格刚毅的人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ldo;是他们!……无耻!……叛徒!&rdo;他怒吼般地重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