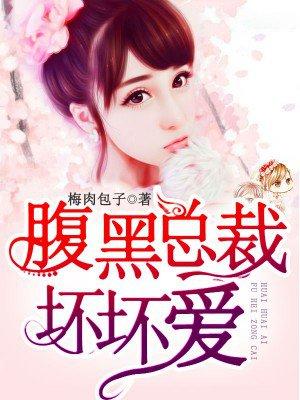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白月光与朱砂痣(穿越) 落日蔷薇 > 第147章(第1页)
第147章(第1页)
孙留芳有些紧张地捏捏帕子,不像从前那样兴高彩烈地上前奉承,反而是拘谨地站在原地,规规矩矩回话。
“最近国公府里事情多,我母亲犯了心疾,她日日在祖母跟前侍疾,所以便不得时间进来孝敬太皇太后,倒辜负了太皇太后的宠爱。”孙妃瞅了她一眼,叹口气道。
“国公夫人病了?那是该好好尽孝道,哪里就谈得上辜负了。你母亲既然病了,你要不要也回府去瞧瞧?”江婧放下手上的花,柔声道。
“谢娘娘关心,母亲病已好转,不碍事了,不用麻烦娘娘了。”孙妃陪着她沿着石台一路走过,“只是母亲年事已高,这一病又牵出几件心事,每日里忧心忡忡,长吁短叹,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着实担心。”
“国公夫人有什么心事?”江婧看了眼孙留芳,关切问孙妃。
“我母亲记挂着家里几个孩子的婚事,如今府里留芳这一辈的女孩子,还一个都没出嫁,她老人家就想着能看她们顺顺利利嫁出去,这心才能放。”孙妃小心翼翼说话,目光不时掠过江婧的脸,揣测她可有不悦之意。
原来他们家打算让孙留芳攀上东宫,便不能为良娣,能进东宫也是好的,不料一场风波,太子被软禁,眼见储君之位难保,孙家哪还敢攀这门亲?若是结了亲,孙家就与这废太子绑到一起,哪还有翻身之力?孙留芳就更不肯嫁了,霍翎虽英挺,但她更想要尊荣之位。
好在先前尚仪局那边虽将京中适龄女子名字收录名册,却也没有明言是替东宫储秀,孙留芳名字虽在上边儿,但一切未落定,在此之前让孙留芳定亲便是,不过孙妃谨慎,还是带人亲自来试探江婧一番,若能让她点头就更好了。
江婧哪有不明白的,脸上的笑没变,目光却淡了:“当长辈的,都操心儿女姻缘。既是如此,可曾替留芳相看合适的人家?”
“看了。”孙妃闻言大喜,“是安平侯。”
“安平侯?”江婧微诧。这安平侯在朝中颇为得势,只是为人刚愎自用,又喜倚老卖老,很不得人心,霍汶也不喜此人,不过对孙留芳来说,最关键的是这人已经年近六旬了,已经死过两任妻子,家里还有四五房妾室,通房和同僚送的瘦马之流尚不计在其间。
“正是,是填房,不过嫁过去就是侯夫人,就可请朝廷诰命,安平侯年纪虽大些,不过最会疼人,家里觉得合适便同意了。”孙妃点头回答。
“门当户对,也好。荣芳,你回头叫尚宫局那边挑几匹宫缎并两副头面赏给留芳姑娘,算是本宫替她添妆。”江婧就不多问,只拿荣芳赐赏。
孙留芳知道江婧是允了这门婚,并没因太子之事为难她,忙跪下领恩。
江婧这回便没免她的礼,受了她的跪拜,忽又叫荣芳:“荣芳,把这盆魏紫、白雪塔与赵粉送到东宫去给太子妃,再拣一篮昨天上贡的樱桃、枇杷过去。”
“是。”荣芳领命退下。
“太子妃的身子如今怎样了?”孙妃闻言不由惊奇,听说这人都快死了,怎还要赏花品果?
“养了两个多月,也该好了。”江婧似笑非笑。
孙妃和孙留芳都纳闷,对望一眼,还没回过味来,就听外头有宫人来禀事。
“说吧,孙妃不是外人。”江婧拿起剪子,头也不回,只在花里挑着。
“禀娘娘,皇上已将围在东宫四周的禁卫军撤回,命殿下即刻前往乾宁宫,另又派于大人带禁卫军在宛和苑将玉阳公主与丽妃娘娘擒住,也已押往乾宁宫。”宫人扬声道。
孙妃与孙留芳大惊。
“可是镇远侯回来了?”江婧却毫无意外。
“是,侯爷也在乾宁殿候着,说是按殿下之计抓到了叛军头领邓维,现正请命领兵追剿余部。”
江婧此时方笑,手中剪子“咔嚓”一声,将开得最美的一朵牡丹剪下,往早已僵愣在旁边的孙留芳头上插去:“姚黄最鲜亮,适合你这样待嫁的姑娘。京里诸多亲郡王家的世子都已大了,本宫原想留着你们好好挑门合适的姻缘,倒耽误你了。”
孙留芳已傻,她到底都做了什么?
……
邓维被抓,魏军踪迹败落,霍汶派下大军全力追剿,西北袁向荣传回捷报,已将萨乌狠狠压制在喀什山脉一带,切断其与苍羌相连之路。玉阳公主通敌叛国,勾结魏军、萨乌在京中私贩欢喜毒,为祸江山,又设计陷害太子霍翎,伙同原萨乌公主苏兰慕、现大安丽妃毒害君王,祸乱后宫,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太子霍翎忍辱负重,协同镇远侯一举铲除压在大安朝心上十多年的祸患,挖出大安毒瘤,又击溃萨乌野心,将迫在眉睫的一场战事消弥,可谓功不可没……
一桩桩,一件件,旨意从乾宁宫传出,无不震惊朝野。
东宫之危即时解除,霍翎威震朝野,再不是昔日年轻储君,帝王之风初现。
江善芷在寝殿困了两个多月,终于得见天日,整个人都松快下来,在庭中拎着裙子放肆飞奔,直到被树上倒垂挂下的人给拦住脚步。
“江姐姐!”左一江笑嘻嘻地倒着看她,在殿里呆了这么多天不见阳光,她脸色苍白许多,如今跑得大汗淋漓,倒叫脸颊浮上些红晕来。
“小……小侯爷。”江善芷气喘吁吁看他。
很久没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