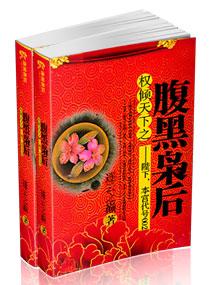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差分机原理动画 > 第135章(第1页)
第135章(第1页)
桌子尽头靠近窗口的一侧,放着三台柯尔特-麦克斯韦尔收报机,其中一台用玻璃罩覆盖着。收报机的纸带卷曲,连接到地毯上安装的铁丝筐里。房间里还有一台弹簧驱动的发报机,配有最新式的维特豪尔加密纸带打孔机。这些设备相配的各种连接线,用勃艮第丝绸严密包裹之后,蛇行到桌面中央一个雕花孔洞里,然后又连接到带有邮局标志的抛光铜盘上,由此穿入护壁材料。
其中一台收报机突然开始打印信息。他沿着长桌走上前去,在纸条从红木基座上出现后,马上阅读上面的信息。
忙于处理颗粒污染但欢迎来访韦克菲尔德
结束
布莱斯端着一托盘羊肉块和酸菜走了进来。&ldo;给您带了一瓶浓啤酒,先生。&rdo;他说着,在一段桌子上铺好亚麻布和银质餐具,这个地方显然就是用来吃饭的。
&ldo;谢谢你,布莱斯。&rdo;奥利芬特把韦克菲尔德的信息捏在指尖上,然后松手,任其跌回铁丝篮。
布莱斯倒好浓啤酒,然后带着托盘和空瓷瓶离开。奥利芬特把办公椅推到食物的位置,坐下来,给羊肉撒上布兰斯顿酸菜粒。
三台收报机之一突然启动,打断了他独自用餐的安静。他转身看去,发现右边那台机器的纸带开始向外传输。韦克菲尔德的邀请来自左边那台机器,那是他个人的联系号码。右边的机器意味着警务信息,比如拜特里奇或者弗雷泽发来的消息。他放下刀叉,起身走了过去。
消息从黄铜出口缓缓吐出。
来自fb请即刻前来弗雷泽
结束
他从马甲里取出父亲留下的德国猎人手表,看了一下时间。把表收起来,抚摸了一下中间那台收报机的玻璃罩。自从前任首相去世以来,这台收报机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
出租马车把他送到布里格森居住区,附近有一条大街,是投机建筑商在古老而神秘的废弃建筑之间拓建的。这里,就是从前的伦敦东区。
从单马双轮车上下来时,奥利芬特就觉得,这个居住区堪称史上最丑陋的灰砖建筑。他估计,那个建筑设计师,目睹这十座监狱一样的凄凉住所逐渐成形,在奇丑无比的房舍完工之前,很可能就躲在附近的酒馆门后上吊自杀了。
出租马车带他来这里的路线,看来也非常适合现在的时间一所有那些街道,似乎都不适合行人,见不得日光。现在下起了小雨,有一瞬间,奥利芬特暗自后悔没有接受布莱斯在家门口递上的雨披。五号楼门口站着的两个人,都披着打过蜡的埃及棉布斗篷,长而且低垂。奥利芬特知道,这是新南威尔士地区的最新改进样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广受好评,非常适合隐藏武器,而这两个人肯定都带着枪。
&ldo;特情局的。&rdo;奥利芬特说着,闪身跳过岗哨身边。慑服于他的语调和气势,对方没敢阻拦。本来,他们都要先请示弗雷泽,才能放人进去。
他走进这座房子,进入一间点着电石灯的会客室。灯安装在三脚支架上,无情的白光被光亮的马口铁凹面反射,显得更加刺眼。会客室的家具看去都是捡来的破烂。有一架竖式小钢琴,还有一台过于庞大的梳妆镜柜,后者的奢华样式在这里显得尤其不协调,上面的金粉肮脏不堪,纷纷剥落。房间里有一块破不溜丢的布鲁塞尔织花地毯,绣着很多的玫瑰和莲花,而周围都是沙漠一样色彩暗淡的粗毛地毯。朝向布里格森居住区院落的窗户上,挡着针织窗帘。窗户旁边有两个悬挂空中的铁丝筐,其中栽种着仙人掌类型的植物,像蜘蛛一样长得乱糟糟。
奥利芬特闻到一股酸臭味,要比电石灯的臭味更刺鼻。
拜特里奇从房子后面出来。他戴着美国人喜欢的高顶常礼帽,以便让他看上去很像每天跟踪的皮克顿的手下人。他很可能用心完善过这套行头,包括侧面粘接的特制靴子。看到奥利芬特,他的表情露出少有的惊慌。&ldo;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长官。&rdo;他磕磕巴巴地说。看来肯定是出了大事。&ldo;弗雷泽先生正在等着您,长官。我们什么都没有动过。&rdo;
奥利芬特跟随他穿过会客室,走上一段狭窄、陡峭的楼梯。上面是一条空荡荡的走廊,点着第二盏电石灯。光脱脱的墙灰上有大块大块的硝酸钠痕迹。刚才的焦臭味儿在这里变得更为浓烈。
又走过一道门,这里的白光更为眩目。弗雷泽抬头看了一眼,他正沉着脸蹲在一具四肢张开的尸体旁边。弗雷泽想说话,奥利芬特用手势制止了他。
这里就是臭味的源头了。在一张老式扶手椅前面,放着一台小小的普里摩牌现代火炉,是通常用于野外的那种型号。黄铜燃料罐像镜子一样光洁。加热环上面放着一口小铁锅,锅里煮的东西已经被烧得焦黑,只剩一摊恶臭的残渣。
他将注意力转向那具尸体。死者是个身材非常高大的男人‐‐在这个小房间里,想走动都得跨过他张开的四肢。奥利芬特躬身打量他扭曲的面容、凝滞的眼睛。他站起身,看着弗雷泽问道:&ldo;那么,你怎么看?&rdo;
&ldo;他正在给豆子罐头加热,&rdo;弗雷泽说,&ldo;从这边的小锅子里直接挖着吃,用这个。&rdo;他用脚趾指了指地上的蓝色搪瓷炒勺,&ldo;我认为他是独自一人。我还估计,在他中毒倒地之前,已经吃光了整罐豆子的三分之一。&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