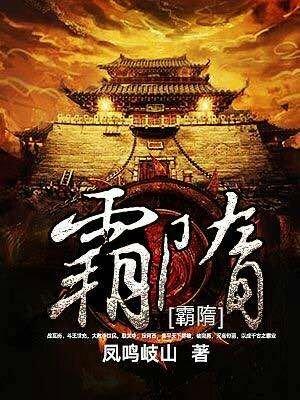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莱茵河之战by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他妈的,”迈克尔自言自语,“我真想死……”
他躺下了,将两封信压在枕头下面。阳光透过玻璃,射到床上。房间里倒是货真价实的暖和,迈克尔陷在被褥中,很快便睡着了。
人为啥不冬眠,是迈克尔从小便迷惑不解的问题之一。他从自然课程上学习到了冬眠的相关内容,也在野地里挖出过冬眠的蛇。要是人能冬眠就好了,每当冬季到来,迈克尔不得不爬起来去上课或干活,他就重新陷入迷思。他如果是头熊该多棒!秋天捡拾各种食物,吃得肥肥壮壮,然后找个舒服的洞穴钻进去,蜷成一团,美美地睡上一觉。等再度醒来,春天已降临大地。他可以跳进溪流洗洗全身的皮毛,然后抓几条鱼填饱肚子——
刺眼的阳光惊醒了迈克尔。他爬起来,发现身处一间干净整洁的屋子里。得去上班了,迈克尔急急忙忙洗漱,抬头照镜子时,惊愕地看到自己两鬓斑白,眼角堆积着细密的皱纹。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劲。他就这样出了门,公寓楼下停着一台不错的车子。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车。迈克尔用凭空变出来的钥匙打开了车门,很快就行驶在整洁的高速公路上。他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上班,每个人见了他都恭恭敬敬。这可真有意思,迈克尔想,我得来杯咖啡提提神,瞬间就出现了一杯咖啡,似乎是从空气中直接跳出来的。
“我想再来份咖喱香肠。”迈克尔说。
咖喱香肠也出现了,热气腾腾。迈克尔试着提出其他要求,全部一一实现。“我具备了超能力吗?”他兴奋地揉搓手指,“还是说,我变成了神?”
“你可以获得任何你想要的。”一个声音轰隆隆地说,“除了一样,我都能为你实现。”
“我想要钱,很多很多钱。”
大捆大捆的美钞堆满了桌子,但这不足以让迈克尔满足。“我希望德国的法律改掉该死的175条。”一本德国刑事法落到钞票堆上,迈克尔翻了翻,欣喜地看到,那条讨厌的法律竟然被删除了。
“那我就没啥好担心的了,”他嚷嚷开来,“我需要我的大学生!卡尔?冯?昆尼西!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不行,”那个轰隆隆的声音拒绝道,“只有这件事无法实现。”
“为什么?”迈克尔疑惑地站了起来,抱着那本德国刑事法,“我需要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因为他早就死了。”声音说,“现在是1990年,迈克,你忘了吗?昆尼西早在1956年就在莱茵河边饮弹自尽。你彻底失去他了。”
“1990年?”迈克尔惊愕地抬起手,就见本来还算光滑的双手急速苍老,布满皱纹和老年斑,一面镜子出现了,镜中人头发全白,老得像枚风干的胡桃。“天哪……”他用皱巴巴的双手捂住脸,“这么多年过去了吗……”
时间就是这样快,从来不会等待。1945的春天彷佛尚在昨日,迈克尔半睁开眼睛,脑中浮现出昆尼西年轻的样子——那身田野灰军装,散开的领口,露出一截白色的衬衣领子。虽然激战刚刚结束,他仍旧保持着洁净的姿态,光笼罩他,他就像个天使……
“唉,这可怎么办,”迈克尔喃喃,脖子酸痛无比,“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
刚才那是个梦,他想起来了。没有1990年,还早得很,他可不一定能撑到那时候。现在是1956年的冬季,冬季,雪即将落下。“圣诞市场,”迈克尔蠕动嘴唇,“弄棵圣诞树……别忘了槲寄生……”
他又睡着了。这次他睡在一张沙发上。这沙发可不怎么样,扶手硬得要命。迈克尔半睡半醒,总感觉有件事还没做。可能是工作,他得多攒点儿钱。玛丽说得对,一个富裕的老单身汉总还能对付过去,要是没钱,那必然要露宿街头。工作,迈克尔动动手指,还好他拥有一家农场,实在不行卖掉农场,那点钱也能凑合一段时日……
啊,这是他的家,农场的房子。得给沙发换套新垫子,软一些的那种。等醒了就立刻开车去城里……就在这时,厨房里响起了细碎的动静,迈克尔努力侧过脸,只看到一个模糊的金色影子。
“你下班啦?”迈克尔下意识说,“今天不加班?”
“不。”影子说,声音遥遥的好像隔着水雾。
“明天加班吗?”
“不。”
“明天休息,去瑞士玩吧?叫上夏莉,问问她和弗兰茨要不要一起去?”
“嗯。”
影子忙碌着,腰背挺得笔直。现在是哪一年?迈克尔说不清楚。1956年?1950年?1975年?……“唉,”他重重地叹口气,“我爱你,”他说,用德语,“卡尔,我爱你。”
影子没有回答。迈克尔等了许久,慢慢撑酸痛的眼皮。鼻子疼得要命,他使劲擤鼻子,庆幸自己仍身处1956年,他的大学生还活在人间,并且有位医学院毕业的法国佬照顾。
“感谢上帝……”迈克尔撑着无力的身体跪下,“求您……”
上帝真的存在吗?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迈克尔坚信神的力量,但上帝似乎厌弃他——毕竟他深爱着一个同性,还做出过那么多不可饶恕的坏事。
礼拜三,迈克尔的感冒仍未好转。他托前来探望的“勺子”帮他买了些吃的东西,堆在厨房的小木桌上。“勺子”居然还买了瓶红葡萄酒,信誓旦旦地说,对付感冒,只消加热红酒喝下去睡一觉,保证第二天就能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