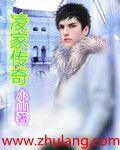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一先令蜡烛读后感 > 第45章(第1页)
第45章(第1页)
&ldo;那么有名?&rdo;她喃喃说道:&ldo;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rdo;
辛格提醒她克莉丝汀最近在报纸上这么出名的原因。不过她更惦记的似乎不是这个女人悲惨的结局,而是她心中那个孩子的成就。
&ldo;她很有进取心,你知道吗?&rdo;她说道:&ldo;所以我才会记得这么清楚。她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其他人都急着要离开学校去赚工资。大部分小学生最想做的就是如此而已,你知道吗?辛格先生,每个礼拜的工资在口袋里,就有了可以逃离家里的吵闹的本钱。可是克莉丝汀娜想上中学。她也真的拿到奖学金了,但是她的家人还是认为负担不起。
她过来找我哭诉。这是我惟一见到她哭的一次,她不是个情绪化的孩子。我请她妈妈来找我。很和蔼的女人,但是缺乏坚毅的性格。我说服不了她。怯懦的人往往会很固执。这是我多年来心中的一个遗憾,因为我失败了。我对孩子的上进心有很强烈的感受。我自己也曾经很想上进,结果‐‐后来我不得不打消念头。所以我能了解克莉丝汀娜的心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离开学校的时候。她到工厂去上班了,我记得。他们家需要钱。她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兄弟,一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妈妈的抚恤金很少。
她终于还是飞黄腾达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ldo;
辛格要告辞的时候,问她怎么会错过报上那几篇关于克莉丝汀。克雷年轻时代的文章。
她说她从来不看星期天的报纸,而其他天的报纸,她好心的邻居提姆森家,会在隔天送过来给她。这几天他们到海边去了,所以她看不到新闻,除了外面的海报以外。
她并不怎么怀念看报纸。一种习惯而已,辛格先生不认为吗?三天没有报纸,想看报纸的欲望就消失了。而且说真的,没有倒还快乐一点。这年头的报纸让人看了很沮丧。
坐在自己小小的家里,她很难相信外面有这么多暴行和仇恨。
辛格继续询问了许多人关于那个冷酷无情的东西赫伯。歌陶白的事。不过几乎可以说没有人记得他。他从来不曾在一个工作上超过五个月(五个月是他的最高记录,在一个铁器商那里),知道他离开了也没有人难过。谁都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不过范恩到南街去访问克雷生前的服装师邦朵,倒是带回来赫伯的一些消息。
是的。邦朵知道她有一个兄弟。一提起他,她皱缩的脸上那对眨巴眨巴的褐眼眨得更厉害了。她只见过他一次,希望这辈子永远不会再见到他。有天晚上在纽约,他递了一张纸条进来给她的女主人,在她的更衣室里。这是她第一次有自己的更衣室,也是她名列在节目单上的第一部戏,那部戏叫做《我们走吧!》。她演得很成功。
当时邦朵负责将她还有其他九位小姐打扮成唱诗班的女孩,但是当她的女主人红遍全世界的时候,她继续把邦朵留在身边。她的女主人就是这种人:永远不会忘记朋友。纸条送进来之前,她一直有说有笑的。可是她读纸条的时候,那个表情就像某人挖起一匙冰淇淋正要送进嘴里,却发现里面有条虫一样。他走进来的时候她说:&ldo;你终于还是出现了!&rdo;他说他是要来警告她,她将有大难临头什么的。她说:&ldo;应该是来看看有什么好处可捡吧,我看你是这个意思。&rdo;邦朵从没见她那么生气过。
之前她刚把白天的妆卸掉,正准备要化上舞台妆,脸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然后她请邦朵到外面去,不过房里开始吵得很凶。邦朵站在门外守着‐‐在那时候,就有很多人想求见她的女主人‐‐免不了还是会听到一些。到最后她不得不进去,因为女主人再不上台就要来不及了。
那男的要她闭嘴,不过女主人说如果他还不走的话,她要叫警察了。于是他就走了,而且在她的印象里从来没有再出现过。偶尔他会寄信来‐‐邦朵认得他的笔迹‐‐而且好像永远知道她们在哪里,因为信上都是正确的地址,不是转寄过来的。
每次收到他的信以后,女主人总会陷入严重的郁闷。有时长达两天,甚至更久。有一次她说:&ldo;仇恨真的很耗体力,你说对不对,邦朵?&rdo;邦朵从来没恨过谁,除了一个习惯对她很不客气的警察以外,不过她是咬牙切齿地恨他,而且她也承认仇恨的确很伤人。像一把火在内心延烧,直烧到你一点也不剩。
除了邦朵对克莉丝汀的哥哥所作的描述之外,还有美国警方的报告。赫伯。歌陶白在他妹妹进入美国之后五年左右也去了美国。他在波士顿一位著名的神职人员家里当过一段短时间的男仆,对方起初显然是为他的举止虔诚所欺骗。他后来因为某种芥蒂而离开‐‐至于是何种芥蒂并不清楚,因为这位神职人员,不论是出于基督徒的慈悲,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担心自己的识人不明受人议论,不愿提起控诉‐‐警方也失去了他的行踪。
然而据信他应该就是那个打着&ldo;神的兄弟&rdo;名号,以先知姿态在美国境内四处巡回的男子,而且,报告上说,最后还名利双收。他曾在肯塔基州因为亵渎神明而入狱,在德州因诈骗罪入狱,在密苏里州因聚众暴动而入狱,在阿肯色州是他自己请求保护,在怀俄明州则因教唆罪入狱。每一次拘留期间他都否认和赫伯。歌陶白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名字,他说,除了神的兄弟之外。当警方对他表示,他们并不会把他和神的关系视为不宜将他驱除出境的理由时,他随即接受了这个暗示而自行消失。关于他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在某群岛‐‐据说是斐济‐‐主持一个布道组织,然后卷款潜逃到了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