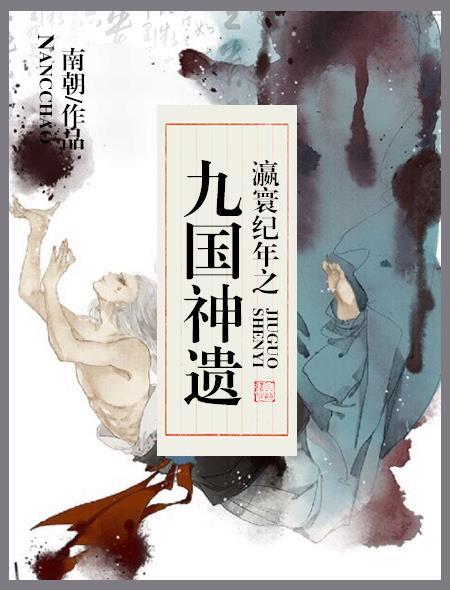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大明太师起点 > 第四百七十七章 背锅的陈嘉鼎(第1页)
第四百七十七章 背锅的陈嘉鼎(第1页)
翌日清晨,一驾豪华的马车缓缓停在广东布政使司衙门前,帘布撩开,年近四旬的陈嘉鼎一脸严肃的走出马车。
他是得到伍士皐召见的消息后赶来的。
通禀的公员也没说什么事,弄得陈嘉鼎一头雾水,心里隐隐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按说这几年,他们陈家顺风顺水,加之自己的父亲又高升去了南京,做了全国工商联的副会长,官面上、地方上谁敢不给他们陈家面子?
这不安之感,没道理。
带着满心的不解,陈嘉鼎面上倒是不露端倪,主持家族事业几年,早也不是吴下阿蒙,这养气沉气的功夫还是有的。
迈步跨进衙门,值守的衙差也都认识陈嘉鼎,自然是不敢阻拦。
大门内进进出出的官员见到更是会亲切的打声招呼,客客气气的喊上一句陈会长。
品轶高些的,还会驻足和陈嘉鼎寒暄两句。
这布政使司衙门与陈嘉鼎而言,和回家没什么太大分别。
一路畅行无阻的进入到伍士皐单人独院的公事房,陈嘉鼎在门外驻足,作揖喊了一声。
“下官陈嘉鼎,谒见藩台。”
正对着房门的位置摆了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年轻公员,早在陈嘉鼎唱声前便已经起身迎了出来。
“陈会长来了,藩台等您多时,快请入进。”
“有劳。”
这年轻人自然是伍士皐的秘书,与陈嘉鼎亦有多面之缘,当下就请陈嘉鼎入内。
屋内,伍士皐端坐太师椅内,此刻正伏案批阅公文,见到陈嘉鼎进来,同样满脸微笑的起身,伸手虚引。
“嘉鼎来了,快坐快坐。”
“多谢藩台。”嘴上客气一句,陈嘉鼎也就顺着话坐在了伍士皐的对面,谢过秘书奉上来的茶水后寒暄一句。
“几日未见,藩台的气色可是越来越好了。”
“咱广东的发展越来越好,一派欣欣向荣,本官喜在心里,相由心生而已。”伍士皐打开抽屉,取出一形如笛子般的物件放到桌上:“办公司送来的上好烟叶,嘉鼎要不要来两口?”
此物为烟枪,乃是广东近年来新发明之产物,陈家买卖做的那么大,陈嘉鼎自然是见过,闻言笑着摆手:“下官不好此道,藩台自便。”
伍士皐也不多客套,见陈嘉鼎拒绝就随手收了起来,继续寒暄道:“嘉鼎进来可都还好?”
“托藩台挂心,下官一切都好。”
“那就行,家里怎么样?”
寒暄嘛,顺口的话,陈嘉鼎应了一声:“也都还不错,就是一切晚辈整日游手好闲,家中几位叔父没少跟着操心。”
伍士皐嗯了一声:“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小辈不争气,咱们做老人的,谁要跟着操心,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加上言路开禁、报业兴盛,这孩子闹出点不成熟的问题,那报纸上就动不动引申到家里,好生麻烦,这朝廷的国法都废株连了,老百姓们反而搞起了株连大狱,恨不得谁家的孩子犯错,让当爹的都跟着吃挂落,动不动就吵着抄家,吵着罢官,就像现在有个新词怎么说来着。”
“仇官仇富。”
“对对对。”伍士皐乐呵起来:“报纸上是这么说来着,搁那些百姓眼里,搞得好像是官都贪、商人都是为富不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