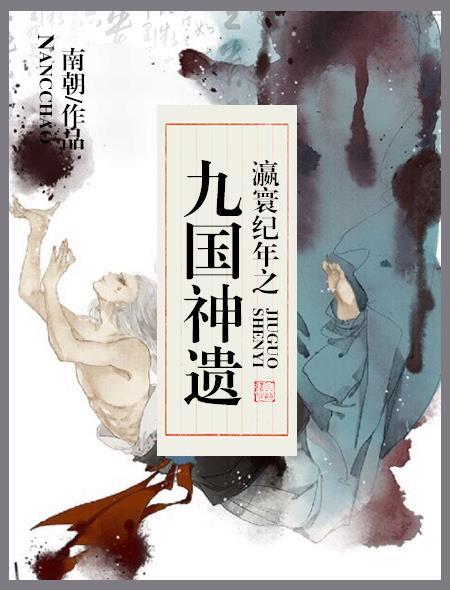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解除婚约后渣攻对白天鹅真香了免费阅读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原来这就是贺明风的“紧急任务”。
原来他不需要香槟,只需要啤酒,他不需要沈凉月,只需要另一个人陪他度过生辰。
自鸣钟响了十二下,一场豪宴只剩下残羹冷炙和阑珊的乐声。沈凉月拿着一把剪刀漫步在锦绣的花团中,他亲手一根根剪断系着氢气球的细线,一个个写着“生日快乐”的气球飘在空中、越升越高。
“我来晚了,这里真漂亮。”贺明风从背后抱住沈凉月,亲昵地蹭了蹭他的头发,带着一身酒气醉醺醺地说:“凉月,谢谢你,对不起啊”
沈凉月没答话,他望着夜色中腾空飘起的氢气球,就像看着渐行渐远的贺明风。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可飘忽的丝线从他指尖溜走,怎么也抓不住,只能眼睁睁地一任气球愈飞愈远。在那一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他们的结局,这份婚约到了最后,他能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句:“凉月,谢谢你,对不起啊”
那天晚上,沈凉月做了个梦。他梦见两个小孩手牵手在花园里玩闹,突然,大孩子甩开小孩子的手,头也不回的转身而去。那个被同伴留在原地的小孩哭得好惨,颤抖的小手向前徒然地伸着,眨眼间变成一只修长的成年人的手,凝成一个苍凉无望的手势。
玫瑰正在无声的凋残。
“刷啦”一声,沈凉月拉开了厚重的窗帘,明媚的阳光扑进堂皇的室内,为他周身都镀上一层光。他并没有如故事里的幽灵游魂,在灼热的阳光中灰飞烟灭,反而神情坚定、眼眸冷淡,傲然地站着,直面所有挑衅和宣战,大宅中反光的玻璃瞬间都变成了他的铠甲,甲光向日、无坚不摧。
在暗夜中溃烂的花瓣、簌簌颤抖的枝条,在黎明的光普照大地时,又变得美而静,仿佛永远盛开、不可侵犯。
“今天的天气不错。”沈凉月回过身,向永远能适时出现的管家点了点头,漫不经心地说:“那位先生还在等?”
“是的,少爷。”
沈凉月摘下眼镜,轻笑道:“他如此诚心,我岂能失礼?”
-
-
苦等了三四个小时,褚飞终于走进了大宅。
“人们都说公爵府邸有帝星最美的玫瑰,”管家引着他走向花园,“我们都为此骄傲。”
在玫瑰花丛中,褚飞看见了端坐喝茶的沈凉月。也许大家说的不是花,而是人,在花枝掩映中,沈凉月比玫瑰更美。他在太阳下站了太久,身上的军服已被汗水浸湿,而沈凉月穿着精致的三件套,端起骨瓷茶杯闲适地喝着红茶,手指比瓷器还要细白。
此情此景已经足够任何一个oga自惭形秽,可褚飞知道自己不能退,他必须要争,如果不争就什么都没有。沈凉月拥有的太多了,只要他愿意,追求者必如过江之鲫,何必还要霸占着贺明风?
“褚先生,早。”
“公爵阁下,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实在称不上早。”褚飞坐在沈凉月对面,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茶,嗤笑道:“平民六七点钟就要起来奔生活啦。”
“所以,褚先生是来为平民福利组织募捐的?”
“不是。”褚飞被他噎了一句,瞧着沈凉月的神情还是淡淡的,难道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来?“我是为贺少将的事来的。”
沈凉月放下茶杯,深黑的眼睛静静望向对面的oga。半晌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名不正则言不顺,褚先生,我希望你之后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褚飞的脸霎时涨得通红,双拳不自觉地紧握、手心里都是冷汗,他已经来了,已经坐在这里,怎么能在这时候打退堂鼓?他要向沈凉月宣战,要主动维护自己的爱情!褚飞霍然抬起头,眼睛亮亮的,一字一字坚定地说:“希望你能放过贺少将,和他解除婚约!”
“放过他”沈凉月觉得可悲又可笑,灵魂似乎飘在半空,冷眼俯视着这场闹剧,他听见自己冷静地问:“为什么?”
“因为他不爱你。”
“他爱不爱我,关你什么事?”
褚飞没答话,突然笑了起来,“你何必自欺欺人?”
沈凉月发现褚飞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和一侧浅浅的酒窝,看上去十分鲜活可爱。原来贺明风喜欢的是这样的oga、这样的笑,沈凉月试着提起嘴角,也笑了笑,可他的眼睛暗沉沉的,没有一点笑意,这个表情更像是冷嘲。
“贺明风让你来和我说的?”
“不是,”褚飞顿了顿道:“是我自己要来的,我希望这件事不要闹得太难堪,让他难做。你知难而退,成全我们,不好吗?”
知难而退!这话说得多好,沈凉月简直想鼓掌!原来褚飞也知道什么叫难堪——这样的会面难道还不够难堪?也许在他们看来,沈凉月的难堪不叫难堪,而叫成全。“你是以什么身份在和我说话呢?贺明风的同事、朋友、还是他的情人?”沈凉月冷冷地说:“我是他的未婚夫,你是他的什么人?”
褚飞一时被他问住,想了很久,才说:“我是他喜欢的人。”
悬在半空冷眼观瞧的灵魂再也漂浮不住,如同被泪雨浸透的云团猛地向下沉,拖着沈凉月的躯壳坠到冰冷黑暗的地狱里。
骨髓血液都冷透了,可沈凉月端坐的姿态竟仍然矜贵闲适,他的手止不住地发颤,但端起茶杯的时候又稳如磐石,他抿了一口热茶,无所谓地笑道:“喜欢是多虚无缥缈的事啊,他今天喜欢你,明天可能又会喜欢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