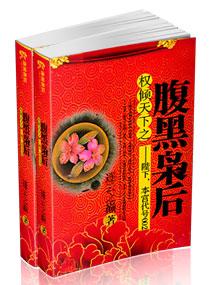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梦见自己要结婚了 别人带我回去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他一定听见了,听见我蹑手蹑脚穿过客厅。我以为他没有,但他听见了。我看过他假睡,看过不下一百遍。也许他只想要她离他家人远一点,也许他想要更多。但当她出现,甩了他一巴掌,表明她才不在乎他想要什么:难以抗拒却又遥不可及的泰瑞莎化身再度出现,麦特的女儿从他身边夺走他想要的一切。也许他喝醉了,直到他察觉自己做了什么。他很强壮,那时候。
屋里不是只有我们醒着。凯文也起来了,或许想上厕所,发现我们两个不见了。对他来说,这没什么,因为老爸经常几天不见踪影,谢伊和我也偶尔会去打工做大夜班。然而,这个星期当他得知萝西是被人杀害的,他忽然想了起来。
我感觉自己仿佛掌握了所有细节,在我听见答录机传出洁琪声音的一瞬间,来龙去脉便已经在我脑袋的深渊浮现,我感觉肺里涨满污浊冰冷的水。
老妈说:&ldo;他应该等我长大的。泰瑞莎很漂亮没错,她真的是,但我到了十六岁也有许多小伙子觉得我很美。我知道我还小,但我在长。他要是肯把那双笨眼睛从她身上移开,看我一眼,一眼就好,一切就不会发生。&rdo;
她语气里的感叹重得可以压沉几艘船。我忽然明白她认为凯文也是因为喝醉了,和他老爸一样,才会从那扇窗子摔出去。但我还来不及纠正她,老妈已经手指按着嘴唇,看着窗台上的时钟惊声尖叫:&ldo;老天爷,你看看,已经一点了!我得吃点东西,否则会虚脱的。&rdo;她扔开圣诞装饰,将椅子往后一推,&ldo;你也来个三明治。&rdo;
我说:&ldo;我拿一个给老爸?&rdo;
老妈转头看了卧房一眼,接着说:&ldo;不管他。&rdo;说完便开始从冰箱里拿东西。
三明治是白吐司夹奶油和碎肉火腿,切成三角形,让我一下子回到脚还碰不到地板的童年时光。老妈又泡了杯浓茶,照自己的方法吃起三明治。从她咀嚼的动作看来,应该换了比较好的假牙。小时候,她总说她牙齿没了是我们的错,每生一个孩子就掉一颗,说着说着泪水开始涌上眼眶。她放下杯子,从开襟羊毛衫口袋掏出褪色的蓝色手帕,等泪水干了,接着擤擤鼻子,继续吃三明治。
第十八章支离破碎
我很想和老妈就这么坐着,每小时热一次茶壶,偶尔做点三明治吃。老妈只要闭上嘴巴,其实是个不错的伴。我头一回感觉厨房像避风港,起码比起外头等着我的世界,这一端安稳许多。我一踏出这扇门,就只剩一作事情可做:寻找确切的证据。这不难,我想顶多二十四小时,但接着真正的梦魇才刚开始。一旦找到证据,我就得决定该拿它怎么办。
两点左右,卧房出现动静,床垫弹簧吱嘎作响,清喉咙的哮喘和震动全身抑制不住的干咳。我想差不多该走了,结果引来老妈连珠炮似的追问一堆圣诞晚餐的问题(假如你和荷莉要来,我说假如,她喜欢白肉还是红肉,还是根本不吃?因为她跟我说她妈妈只买自由放养的土鸡肉……)。
我只管低头往外走,踏出门口的时候,她在后面喊:&ldo;很高兴见到你,改天见!&rdo;老爸含着脓痰的嘶吼,从她背后传来:&ldo;乔茜!&rdo;
我甚至晓得他怎么知道萝西那天晚上会去哪里。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伊美达,而我左思右想,老爸会找她只有一个原因。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消失两三天是去找酒喝,即使发生那么多事,我也从来没想过他会背着我妈偷情‐‐就算想过,我也觉得酒精让他根本做不了什么,我家还真是惊喜不断。
伊美达得知萝西的计划之后,也许直接告诉她老妈‐‐母女情深、吸引关爱,谁晓得‐‐或者在我老爸面前约略提起,让她觉得自己胜过搞她母亲的家伙。我说过,老爸不是笨蛋,他自己会拼出答案。
我按了伊美达的门钤,这回没有人接。我后退看看窗户,窗幔后而有东西在动。我又按一次,按了整整三龠钟,直到她一把抓起对讲机说:&ldo;干吗?&rdo;
&ldo;好啊,伊美达,我是弗朗科,意外吧?&rdo;
&ldo;妈的,滚开。&rdo;
&ldo;哎呀,小美,别这么凶,我们必须谈一谈。&rdo;
&ldo;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rdo;
&ldo;真狠。我没地方要去,所以我会在马路对面等,待在车里,直到你肯谈为止。一九九九年的银色奔驰。你要是玩腻了就来找我,我们简单聊聊,之后我就再也不烦你。要是我先腻了,我就找邻居问你的事,听到了吗?&rdo;
&ldo;你滚!&rdo;
她挂上对讲机。伊美达这个人很拗,我猜至少要两小时,甚至三小时,她才会受不了来找我。我回到车上,转开音响听奥蒂斯&iddot;瑞汀的歌,放下车窗和邻居分享,随他们去猜我是警察、毒贩还是讨债公司。不管猜谁,在他们眼里都不是好东西。
这时候的哈洛斯巷很安静,一个拿着助行器的老头和一个擦着铜器的老太婆絮絮叨叨批评我,两个年轻辣妈购物回来,斜斜瞪我一眼。一个男的穿着闪亮运动服,带着一大堆问题在伊美达屋外东摇西晃了四十分钟,每十秒就用仅存的脑细胞对着顶楼窗户大喊:&ldo;戴可!&rdo;但戴可不理不睬,那男人只好跌跌撞撞走开。三点左右,一个女的走上十号台阶开门进去,显然是夏妮亚。从桀骛不驯的下巴仰角到&ldo;操你妈的&rdo;昂首阔步,她简直就是八十年代装扮的伊美达,让我不晓得该难过,还是该充满希望。只要肮脏的窗幔一动,我就朝窗子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