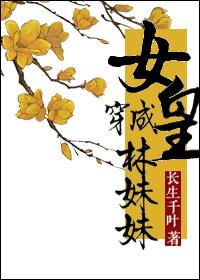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两朝凤仪 百度 > 第一百九十八章 先生(第2页)
第一百九十八章 先生(第2页)
“你嫁了先帝,应是极好的,先生与学生的缘已了,我理应淡忘才是,却没想回江南七年,山水相隔,我日日想的,都是小十三有没有长高,字有没有好好练,宫里有没有受欺负,先帝对你好不好,岁岁年年如织缠。”
公子翡的一番话风轻云淡,一笔带过这些年他如魇缠身的困局,还有那些为了寻解犯下的罪,比如锁了曹家女三年,又比如,七年避而不见,将她的名字设为禁词,而杀的犯禁人。
为什么,挥之不去,偏偏是你。
“当然了,这都是我自己作孽。从前小十三有先帝,如今有东宫,吉祥铺的人也都还不错。”公子翡轻轻加了句,眸色在灯火下晃,“呵,小十三你应是过得极好的。”
话带了暗暗的凉,和涩意。
程英嘤鼻尖发酸,颤抖的伸出手,去触碰他,去碰那袭紫衫,指尖萦绕上他的温度,儿时山水迢迢的梦,化蝶。
“我一直都是念着先生的。只是七年杳无音信,以为先生厌了我。”程英嘤扯着男子衣角,像个犯错的孩子,低低絮语,“或许厌我话太多吧。”
公子翡噗嗤一笑。于是这一笑,江南杂花生树,游人只合江南老。
是了,那时的小十三,话很多。
……
“先生,紫藤花真如名字一般,是紫色的么?”第一堂课,屏风后的十三千金就快嘴快语。
正在讲《弟子规》的少年郎一愣,这冷不丁的发问,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当然是紫色的。”良久,他应,旋即又肃了语调,“好好听课。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刚才讲过的这句是什么意思?”
五岁的程十三自然答不上,隔着屏风挨了顿训,满脑子却都是紫藤花。
然而接下来的七年里,少年郎发现,这小千金脑子不知道是怎么长的,人是坐在这儿,心思却能满天下飞。
一会儿冒出来句“先生,上元灯节那天,安怀门外真有十丈高的火树么?”,一会儿又扯到“先生,秋天玉山的枫叶,真的能红到天际去么?”,想东想西,天南海北。
虽然他总是训她好好听课,但也忍不住会认真回答她,温柔的,耐心的,一遍遍说给她听,是,有十丈的火树,秋天玉山红遍。
忽的有一天,他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极其普通,寻常人出门逛一圈,什么都知道的,近乎于常识。
然而屏风后的小千金不知道。
从有记忆起,就被锁在这道朱门后,富丽堂皇的岁月里,她唯一能见的,是鎏金天井上四方的天空。
还有除了她那个父亲以外,唯一从“外边”来的他,她的教书先生。
他明白的,从给苏仟抗荷花糕进京,见着别邸朱门后的奶娃娃,到接了榜,心甘情愿踏进这道幽深的门,他就选择了她。
他寂寞的,小十三。
……
“我,从来没有厌过小十三。如果说一定有,那也只是厌我自己,我的逃避,和愚蠢。”公子翡伸出手,轻轻拉住了手臂上的小手。
十四年时光啊,他终于,也触碰到她了。
凝脂的肌肤,微凉,水葱段似的指尖反过来,也缠住了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