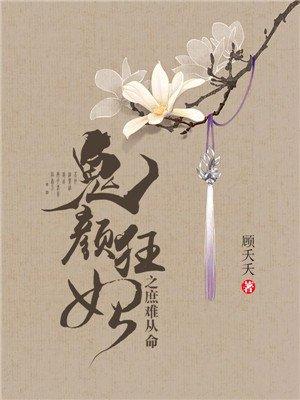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残虐记豆瓣评分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ldo;我口渴了,我要喝水!&rdo;
健治用他那皲裂的手粗暴地堵住了我的嘴。脚步声渐渐远去,变成了下楼的声音。我垂头丧气,但附近还有人居住这一令人鼓舞的事实,又让我恢复了一些体力。那时我竟没有太在乎健治粗糙冰冷的手,以及指甲里的污垢。
&ldo;水在水壶里。&rdo;
健治指着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满是黑烟灰的铝制水壶。
&ldo;叔叔,我要去喝水,把我脚上的铁铐拿下来吧。&rdo;
我恳求道。
健治皱起了眉头,一副很为难的神情。
&ldo;我可不是什么叔叔。&rdo;
&ldo;那我叫你健治好了。帮我把铁铐拿下来吧,我这儿好痛!&rdo;
健治观望了一会儿连接着我脚踝与床柱的手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了铁铐。我细细一看,原来是副玩具手铐,就算靠我自己的力量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开。
&ldo;我上班去了,老老实实待在这里。要不然我就不给你饭吃,不给你水喝哟。乖乖的话,三点钟发的点心我也会拿回来给你,太太常给我们豆馅包。&rdo;
我重重地点着头,开始时健治有些不安地看着我,紧接着他打开了房门,走出去之前还关掉了房间里的灯。门关上了,外面传来上锁的声音,健治在走廊上走远了。现在正是阳光四射的早晨,我却一个人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
我从床上爬起来,望着糊着黑纸的窗户,心想:撕掉黑纸不就能看见外面了吗?这时的我渴望见到阳光,这欲望是如此的强烈,它已超过了我想把自己被困于此的消息告诉别人的欲望。一个人被囚在一间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暗屋子里的恐惧,是无法言喻的,说不定健治也不会回来了,那我将被关在这漆黑的屋子里度过一生,最后死去。想到这里,我被突如其来的恐慌所包围。我走下床来,摸索着向窗户边走去。
窗户完全被钉死了。因为窗缘从上到下全钉着胶合板,黑纸是贴在胶合板上的。这样一来,房间里的灯光不会外泄出去,而在外面看来,这屋子就像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空屋子。绝望中我还在想能不能扳下胶合板,于是用力扳了起来,但是我的手指只是毫无意义地碰了碰牢牢固定着胶合板的钉子头。
突然,&ldo;轰……咚&rdo;,外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我大吃一惊。紧接着&ldo;咻&rdo;地一声,仿佛空气被压缩了,之后又是一次&ldo;轰……咚&rdo;砸碎东西的声音。令人不堪忍受的巨大声响摇曳着室内的空气,有规则地重复着。仔细一听,能辨别出是两台机械按各自的节奏不断地重复着&ldo;咻&rdo;、&ldo;轰隆&rdo;的声响,没有一刻的停顿。
原来健治工作的地方是个有着如此噪音的工厂,我捂住耳朵,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每一次&ldo;轰……咚&rdo;的声音传来时,地板都会随之震动,并&ldo;嘎啦嘎啦&rdo;地响起来,房间里所有的器物,床、寒酸的桌子、刮胡刀、水壶……也跟着&ldo;咯哒咯哒&rdo;地发出响声,连我的身体也像带电一般与轰鸣声共振起来。
&ldo;救救我‐‐!&rdo;
在那震耳欲聋的声响里,我的呼救失去了一切意义。就在这一刻,我开始意识到,表面愚笨的健治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狡猾男人。他把我囚禁于此,是因为他知道工厂的噪音会遮盖住我的行动。我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与烦躁之中,不由得垂头丧气起来,在时断时续地摇晃着的榻榻米上,我几乎失去了知觉。那时,我真的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我现在正在努力,要把那个时候的记忆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那时只有十岁的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意志,即所有的能力来寻求生存,我要想尽办法记录下那个时候的经过。但我没有信心是否能用文字传递出当时我的绝望与希望,纵然我是个擅长使用文字的作家,但要用我现在的文字再现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显然还是很困难的。
我并不是在示弱,我的顾虑大概源于我知道现在的我比起十岁的我来得更脆弱,而且当我成长得越发理性时,准确描摹记忆的能力也就是我对当时的感受就已衰退了。例如,在如今的我看来,十岁的我在健治的房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早晨在工厂轰鸣的噪音中失去知觉的一幕是难以置信的。与其说在噪音中失去知觉,现在的我更愿意相信健治的暴力是残酷的,健治对我的侵犯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当细细回味过去时,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新认识。我发现当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被不可抵御的轰鸣声包裹时,其恐惧远远大于和健治在一起时的恐惧。当时我害怕孤独;而健治虽然可怖,但他逼迫我发挥无穷的想象力,这能让我触摸到自己生命的脉动。
工厂的轰鸣声停止了,周围突然变得死一般地寂静。房门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原来是中午休息时间到了,健治回来了。他闯进屋来,同时带进一股浓烈的荞麦面味道。他首先打开电灯。我的眼睛因为灯光的刺激而一时睁不开,于是继续横卧在榻榻米上,努力找回现实的感觉。
健治高高举起手中的铝制托盘:
&ldo;阿美,吃饭的时间到了哦,肚子饿了吧!&rdo;
健治的声调异常甜美,让我想起他喂养的猫,而在健治眼里,我只不过是像猫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