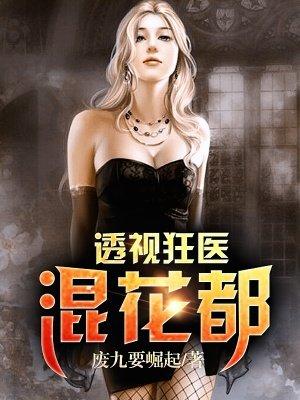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相乱欲何如什么意思 > 第147章(第1页)
第147章(第1页)
“还有吐蕃人!会州和原州就在他们的边境之上,既与大唐结为甥舅之国,突厥人这样猖狂,为什么拒绝派兵相助!”韦后将吐蕃送来的国书往地上一扔,“兵部修书求援,他们竟敢下国书来请求和亲!要我们送公主过去才肯发兵?他们是忘记了五年前是怎么被大唐打得不敢越界的吗?如今竟敢趁人之危,犯我天颜!大唐一定要发兵,一定要打过去!”
韦后独自在阶陛上振振有词,坐在主位上的李显却是一言不发,身为兵部尚书的宗楚客掂量着兵部的家底,也不敢出声附和韦后的豪言壮语。韦后扫视一眼不敢与自己争锋的群臣,忽然意识到有人没有来:“上官婉儿呢?圣人命她主持朝政,朝廷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来上朝!”
“昭容……昭容她去户部查账了……”有官员小声回禀。
“都什么时候了,还去户部查什么账!”韦后用愤怒来掩盖自己面对战事的不知所措,不容李显说一句话,她便直接用手指着外面,传令道,“翊卫在哪里!让上官婉儿回来议政!”
其实从接到被敷衍送回的军报起,婉儿就立刻动身去了户部,那一夜长安城里为了安乐公主的婚事狂欢了一宿,户部却挑灯夜战,把算筹摆了一宿。有了吏部越权行事的前车之鉴,婉儿也不敢相信户部报上来的钱粮名目,拣择与战事相关的几个仓库,实地查验一番,再将数据一核算,果然在户部充盈的账目下,实际的仓储早已被蚕食得不堪入目。
从户部度支的名目相当繁多,包括安乐的大婚、婚前置办的宅子、梁王私宅的修缮、皇后别苑的建筑,乃至宫中禁苑饲养珍禽的开支,尚膳局为满足公主宴饮苛刻需求的鲜品……最近的一例,竟然是为上官昭容置办宅第,没有写皇后的授意,也没有婉儿的签名,户部理应拦着的事情,全都由皇后力荐的户部尚书杨再思亲自操刀办理,这些本应由皇帝内帑出资的项目,全都由国家和民众买了单。
比这更加糟糕的是,那天不许婉儿过问的三百名县官只是冰山一隅,这些食民禄的“硕鼠”在短短一年间已经遍布,他们兼并前朝力推政策发给百姓的受田,成为一方地主,百姓要向朝廷和地方官交两份税,甚至朝廷该收的赋税收不上来,大宗的钱粮反而落入了地方官的口袋里。朝廷第一年的财政就是赤字,前朝积累下来的钱粮像被投入了无底洞,急速地消减下去。
婉儿刚刚还朝时,在六部中就尤其注意吏部、户部和兵部,如今越发确定,这样的骇事,是由吏部开始的大腐败。武皇最讨厌拔擢官员先看门第,不仅是武皇踩着门阀上位所致,更表现出武皇集权的决心。官员一旦把门第看得比皇帝重要,就会各为其主,陷入无穷无尽的党争,武皇扩大科举、开创殿试,其实都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她一生都在努力打破门阀,却在宾天后仅仅一年,就被她的儿子把门阀的案翻了过来。只不过如今的新门阀既不是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又不是功臣新贵,而是欲望永不能平的皇后,和地位尴尬唯有发展势力才能自保安全的梁王。
吏部选官一旦出了问题,这些不学无术只会谄媚上司的下臣,不知忠君为何物,不知报国有何门,更不知体恤下民,不明白县官是国之根基。于是户部的亏空便理所当然,这些官员只知道自己对出身门第的责任,不知道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地方官为自己敛财,分得应纳赋税的一部分去“孝敬”门第;中央官也为自己敛财,分得户部大仓的一部分去“孝敬”门第。钱粮落入门第手里,用以修建豪宅和运输山珍海味,奢侈的生活怎么可能有尽头?于是钱粮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些不必要的消耗品里,朝廷的仓库越掏越空。
户部的仓空了,由国家养起来的军队就断绝了粮饷来源。边关屯田,士兵拿的是朝廷和屯田的双份粮禄,朝廷把粮饷克扣下来,士兵就只能自食其力,本就有被朝廷抛弃的无力感,有名望的将军坐镇时,尚可稳定军心,一旦将军无过被调走,军心就更加容易动摇。士兵的钱粮没有保障,将军里又混杂着靠门第晋升的庸人,这些人占据了军功升职的位置,士兵作战便毫无动力。在这样的军政大势下,婉儿荐张仁亶回去领兵已经是冒险之举,偏偏连这样的建议也不被允许,横遭了韦后的猜忌,用稳不住军心的沙吒忠义,其实沙吒忠义又何尝不是冤屈?
用人不当,就会盘剥本属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没有经济支撑,战争就必然失败。其实在这三类事务中,但凡有一部的尚书看得清,但凡有一个监察御史能直言,冒死进谏一番,或是对立操作一阵,都不会使鸣沙的战事迅速败绩。可偏偏吏部尚书韦巨源和户部尚书杨再思都是韦后的门第,兵部尚书宗楚客是武三思的门第,三个重要的职位,都被门第之官占据,形成了这个败坏朝廷的闭环,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败。
“昭容!皇后请昭容回去上朝!”忙忙碌碌的户部门口,跑来宣政殿的翊卫。
账已查完,本就要回去议事了,婉儿放下账目,闭了闭眼消除用眼过度的模糊,起身跟着他去:“走吧。”
庄严肃穆的宣政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位常秉军国大事的上官昭容身上,仿佛只要她一站上朝堂,再艰难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办法。
吐蕃送来的国书被韦后扔在地上,没有人敢上去捡,于是婉儿进殿时便一眼看见,俯下身,轻轻把它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