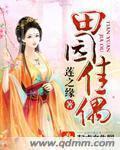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女商大清药丸TXT > 第729章(第1页)
第729章(第1页)
男女各分几桌,桌上热气腾腾,中西菜品大杂烩。烤春鸡、炸猪排、烧鹅仔、城隍庙的酒酿圆子、熏鱼、火腿、臭豆腐干、生煎馒头、蟹壳黄、西洋黄油糖……一看就是调和众口,每人都贡献了一点。
炉子上热气腾腾,煨着每斤一角两分的上品绍兴花雕。
中国人传统上讲虚岁,但此时上海华洋杂处,西历农历并存,为了登记交流方便,人们已经学会熟练地换算周岁。林玉婵今年二十周岁整,算下来在大清打拼已有五年。近日市场平稳,生意如常,她觉得该给自己回馈一个生日,于是偶然跟身边人提了一下。
不过也就是说要好好吃一顿。毕竟这年代年轻人也不怎么张罗过寿;可是不知谁起的头,整了个跨公司团建大联欢!
而且其中一个桌子正中间,还摆着个最近流行的糖霜巧克力蛋糕,并且按照在西方也算很时髦的习惯,插了根粗粗的蜡烛。苏敏官跟身边人讨个火,把那蜡烛点燃。
“林姑娘,吹吧。”
林玉婵忽然眼眶发热。
上辈子她只活了十八岁,尽管是孤儿,但国家照顾着,让她吃得饱穿得暖,幸福得浑浑噩噩,不知人间疾苦。
记忆最深刻的大概就是生日。很多孤儿不知自己的生日,于是每年统一过一次集体生日,大家围着蛋糕和蜡烛唱歌跳舞,就是能盼上一年的节日。
蛋糕上奶油多,孩子们玩疯了时,抹一指头在别人脸上,老师通常也宽宏大量地装没看见,不算浪费粮食。
而今日,能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晚清时节,过一个有蛋糕有奶油有蜡烛的生日,林玉婵喉头有些失语,不知该感谢谁。
她忘记吹蜡烛,低声说:“谢、谢谢各位……”
常保罗肃然起立,端起一张写满字的纸,抑扬顿挫道:“贺寿小令三首,请林姑娘赏光品评……”
苏敏官、容闳和老赵窃笑起来,不用说,想到保罗早年的糗事。常保罗脸皮一红。
不过大多数人不知往事。徐建寅满目期盼,双手托腮,等着听诗。
“记得前时……又是今年事……人如醉……”
平心而论,写得真不错。至少水平比四年前没退步。
要知道常保罗近年专心赚钱养家,已经极少划水偷懒,绝无上工时间构思小令投稿报社的行为。如此疏于练习,还保持了原来的水准,大家纷纷鼓掌。
吃到一半,忽有信差叫门。
奥尔黛西小姐深居简出,不来凑中国人的热闹。但是送了林玉婵一副开了光的银十字架,作为生日礼物。
林玉婵笑着谢了,在胸前比划一下,就不戴了,珍而重之地装到首饰盒里。
“等等,还有呐。”信差笑道。
居然是一副小型油画。土山湾孤儿院的油画课开了两年,培养出一批有绘画天赋的孩子,除了绘制高端茶叶罐、给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绘制插画,不时也接点私单,给在沪洋人绘制肖像、给教友提供圣像之类,俨然已能自给自足。近来孤儿院搞感恩活动,捐款超过一定数额的金主,不论华洋,都让孩子们绘了一幅小肖像,作为回馈。
众人纷纷撂下筷子,围上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