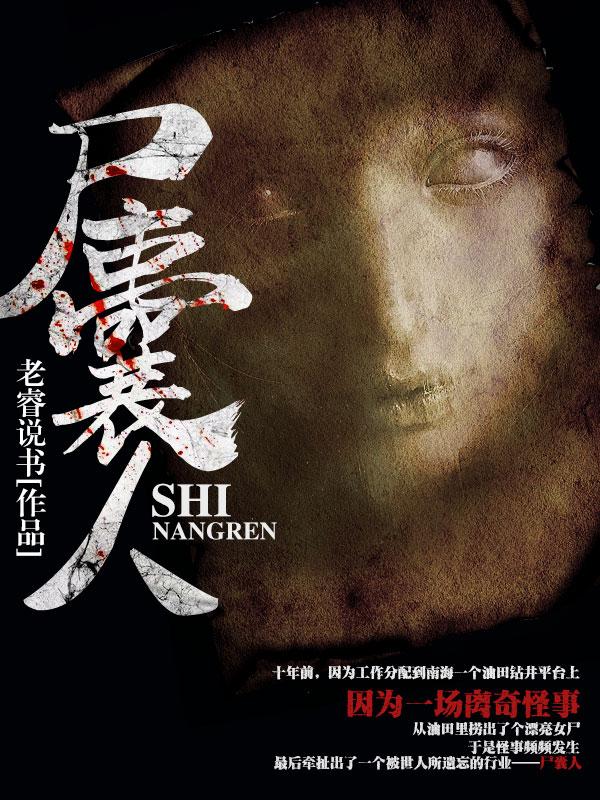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万万没想到准太子是我TXT > 第143章(第1页)
第143章(第1页)
杨景澄道:“我先请人去与你们老太爷打声招呼,叫他别忙着处置。我想你也不放心姑娘,且先回吧。早则今日,迟则明日,便有信了。”又喊叶欣儿,“赏妈妈些茶钱,再叫个车,送妈妈回去。”
吴妈妈连忙摆手:“不敢要世子的赏,我身上还有钱,自己喊个轿子就成。”
杨景澄微笑道:“自古忠仆难得,你这几日的作为我看在眼里,该赏。现不好露了痕迹,改日我送些料子去府上,给你们主仆裁衣裳。”
吴妈妈抽了抽鼻子:“谢世子。”
杨景澄又问:“寄居在旁人家里,多少有些不便。你们姑娘还有什么难处没有?如果有,现告诉我,可别藏着掖着的。旁的都是小事,姑娘不受委屈要紧。”
吴妈妈鼻子一酸,险些又掉下泪来。好半日,终是涨红着脸道:“旁的没什么,就是姑娘现病着,怕她有开销,手头有些紧。”
杨景澄知道齐成济发迹晚,且名声还好,并不是什么大贪官。既不贪,难免穷些。家里那多孩子,顾不上个外孙女也是有的。何况颜舜华的亲娘是庶出,当家的外祖母多少有些偏心,想必日子是不大好过。
于是爽快的命叶欣儿捡了包二十两的碎银子,交给吴妈妈,叮嘱道:“没有了再来问我要,便是没有这一桩,看在我们小时候好的份上,我也不能亏了她。”
吴妈妈接了银子,又给杨景澄磕了个头,哽咽道:“世子是个好心人,菩萨看着呢,定保佑世子长命百岁,子孙满堂!”
杨景澄笑笑,命人送她出去,自己也打马朝北镇抚司衙门去了。不是他性子急,只是时下礼教森严,对女眷尤其的苛刻。他怕自己去晚了,齐家闹出什么风波,把那丫头逼的寻死倒不好了。尤其是那日他确实有些思虑不周,再怎么着也得偷偷的治伤,而不是当着那么多人行事。得亏他现没老婆,不然可真不好收场。
很快走到北镇抚司,杨景澄也不去所里,径直往正堂寻华阳郡公。他这两日原在家等着吏部的调令,此刻赶来衙门,华阳郡公料定有事,便放下手中的笔,直接问:“何事?”
杨景澄看了看左右,恭敬道:“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华阳郡公挥退了左右,道:“说吧。”
杨景澄只得又把昨日的经历与今日吴妈妈报信的事重复了一回,末了看向华阳郡公,陪着笑脸道:“如今形式紧急,我父亲又跟齐侍郎不熟,求哥哥去给我说个媒!”
华阳郡公险些被口水呛着,以他在外的凶名,这小子确定是要他去帮着结亲而不是结仇?
再次看了看左右无人,杨景澄大着胆子挨近了华阳郡公,嬉皮笑脸的道:“好哥哥,救人如救火,你帮我一帮吧!我倒是可以请旁人,只怕旁人没那个脸面,叫齐成济那老学究打了出来,再逼出了人命,你弟弟我就没媳妇儿啦!”
华阳郡公心累的道:“我从没替人说过媒,寻我干这样的事,你脑子里怎么想的!?”
“有什么要紧!谁还没有个第一次!”杨景澄笑道,“朝廷郡公去说媒,天大的体面!就当给我媳妇一个面子呗。”
华阳郡公黑着脸道:“不去!”堂堂锦衣卫指挥使,令朝廷上下闻风丧胆的存在,跑去别人家里说媒,他丢不起这人!
可杨景澄却不依不饶,他此生最恨老学究,大清早的听闻齐成济不干人事,诚心要吓他一吓,遂缠着华阳郡公不肯松口,绕着圈儿的磨着。
华阳郡公恨的咬牙切齿,这小子是吃准了自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是吧!?气的腾的站起身,一个擒拿就向杨景澄抓去。杨景澄反应亦是极快,脚步一侧,身形一偏,就躲了开来。随即一个扫堂腿,逼的华阳郡公后退了两步,趁着他没站稳的当口,纵身扑了上去。
华阳郡公一惊,不待他回避,杨景澄已来到了他的身前,一拳挥出,拳头带着劲风直袭面庞!华阳郡公方发觉自己避无可避,正想伸手格挡,那拳头便停在了他的脸旁。鬓边的发丝叫拳风带的飘起又落下。杨景澄收拳后退,拱手道:“哥哥承让!”
华阳郡公抬腿就是一脚,直踢在杨景澄的大腿上,踢的他嗷的惨叫一声!方整了整衣裳,坐回了椅子上,淡淡的道:“不去,别闹!”
杨景澄毫无形象的趴在案台上看着华阳郡公:“好哥哥,别那么不讲义气!你打也打了,训也训了,再坐着不动,不够意思了吧!?”
华阳郡公懒得理他,自顾自的批着手上的文书。杨景澄也不恼,就趴在他案头,一直不停的碎碎念。一时说他媳妇多可怜,父母双亡没人疼,急需有人去给她做主;一时又抱怨华阳郡公冷心冷肺,半点不讲兄弟情义。直把华阳郡公念的脑袋都快炸了,他竟不知道杨景澄有那么多话讲,居然能讲半个时辰不带重样的!
最恨的是,当这货终于讲完的时候,以为他要停下了。却不料他深吸一口气,抢了桌上的茶盏灌了一大口水,接着重头开始念!
华阳郡公差点就崩溃了,赶上这么个能歪缠的兄弟,打也打不过,吓也吓不走,还不能叫人把他绑了拖出去打板子,只把他梗的胃都疼了。足足折腾了个把时辰,华阳郡公终于绷不住,咬着后槽牙道:“你给我滚!我下了衙就去!”
杨景澄闻言大喜,又一叠声的夸华阳郡公不愧是宗室里最靠的住的,是他的好哥哥云云。气的华阳郡公抄起个镇纸就砸了过去,厉声喝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