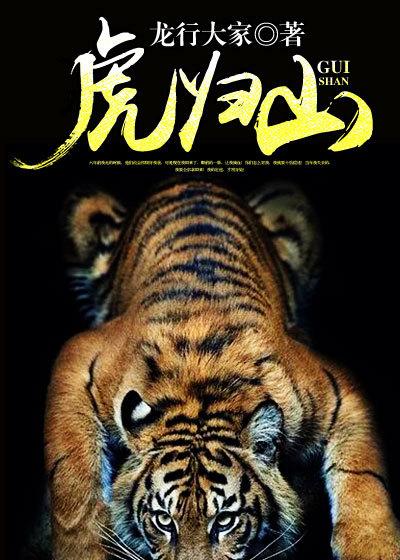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晨光搁浅 微盘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我望着宗晨,说:&ldo;接受手术,有条件。若失败了,请你不带任何留恋的离开。&rdo;
&ldo;不会失败的,浅浅,&rdo;他握着我的手,&ldo;卫衡已经很棒了,还有几位全国移植科最有经验的医生。&rdo;
&ldo;你先答应我。&rdo;我泪眼婆娑的,觉得自己特矫情,可没办法,到这份上了还不矫情,以后便没机会了。
&ldo;那好,我问你,如果成功了,你还赶我走吗?&rdo;他的下巴忽然绷紧了。
我一时为难起来,不赶吧,我是有男朋友的人,赶吧,心里又实在过不去。
&ldo;要是我说不赶,卫衡给我动手术时,会不会不小心手那么一抖?&rdo;我斟酌再三,小心翼翼开口。
&ldo;会。&rdo;一个声音传来‐‐竟是卫衡,他站在门口,一本正经。
我立刻白了脸,哪有这样公私不分,没职业道德的医生。
&ldo;你放心,&rdo;宗晨也严肃起来,&ldo;公平竞争。&rdo;
&ldo;去,谁和你竞争,她现在就是我女朋友。&rdo;
我当机立断,转移话题:&ldo;不如商量手术时间。&rdo;
事实上,早在我同意以前,爸爸便和卫衡瞒着我申请移植的心脏,又托了些关系,到底是申请到了,手术时间定在下个月。
主刀医生那栏,赫然写着卫衡。
我真吓一跳,揪着卫衡问:&ldo;医院不是有回避原则。万一你情绪激动,真手抖了,怎么办?&rdo;
他又给我来了个爆栗。
&ldo;若我没尽力,&rdo;他笑,笑容柔软而懒散,几乎晃了我的眼,&ldo;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rdo;
我无话可说。
时间太瘦,指fèng太宽。这一个月,似乎飞一样的快。
宗晨自我住院后消失了几天,又重新出现,身边还带了个同样沉默寡言的助理。
白天那助理时不时在病房外晃悠,晚上则是宗晨自己过来。有时忙了,也带着手提和资料,久而久之,甚至连那阅兵式一样整齐的铅笔都搬来了医院。
我逗他:&ldo;你不是移民了?&rdo;
&ldo;谁规定移民不能回来?&rdo;
我又讽刺:&ldo;你工作流动性还真大,一会伦敦,一会杭州,哪个老板有了这样的员工算是倒霉。&rdo;
他挑挑眉:&ldo;不好意思,我的老板是自己。&rdo;
告诉他,我爱他。
我终于爆发:&ldo;一个面瘫也就罢了,白天还叫另一个面瘫守着。不知道这会影响病人心情?&rdo;
&ldo;你歪心思那么多,谁知道会不会跑了。&rdo;他笑,&ldo;我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rdo;
头儿从西藏回来后,便也匆匆赶过来,抱着我便哭天喊地,被宗晨给制止了。
他只淡淡说了一句:&ldo;省点眼泪,她会没事的。不如帮我在上海找处好的写字楼。&rdo;
头儿很及时的收回眼泪,以工作第一的原则,迅速联系下属。
我问:&ldo;你找写字楼做什么?&rdo;
&ldo;开个工作室。&rdo;
&ldo;哦,叫什么名啊?&rdo;我忽然兴致勃勃。
宗晨皱了皱眉:&ldo;这倒没想过。&rdo;
&ldo;叫粽子吧,多形象。&rdo;我又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