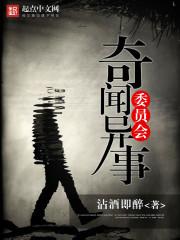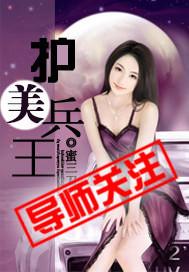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他开局一个碗TXT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收受了贿赂会对朱元璋有些好感,送回他们同朝的官员却会让他们对朱元璋的警惕降下许多,比起好感,降下警惕才是朱元璋现在最需要的。
“但若是元朝因此要奖赏将军什么名号称号的,还望将军一定推脱不要。所谓走兔死,良弓藏,被招安了是一分钱好处也没有的。”
“这个自然。”朱元璋笑容中带上了些冷意,接受朝廷的封号怕是就要四处被朝廷渲染成招安军了,不说别的,他军中那些反元的士兵都要与他离了心了,他自己也深恨元朝不可能当元朝的走狗。
两人又就当今局势聊了一番,都觉得现在还是应该好好发展如今手下地盘的农业经济,不用急着扩张,越是交谈越是觉得意见相合,十分投机。
“若是将军得安天下,准备怎样做?”说着说着两人便说到了安天下之后的事儿,虽然还遥不可及却让人忍不住对之心生向往。
朱元璋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治国可松,立法当严,与民休养生息也不忘抵御外敌。首先应当擢拔良才选之为官,外设监察机构体察民意管理官员。”李善长也就实话实说了。
朱元璋为他鼓掌道:“宽严并济,内忧外患都被你考虑了,甚至连监察官员你都想到了,你确实是个良才。”然后他站起身,负了手背对了李善长道:“只是还不够。良才从何而来,何人可为监察,若是监察者中出了腐败者又该当如何,若是建国,架构一个结构实在有许多要考虑的,都需看情况而定,因此这不是首先要做的。”
“那将军以为如何?”
“首先啊我要统计全天下人口,重新丈量土地分之与民,在天下铺设道路,使这广阔土地四方八达无处不可去。”朱元璋想起姜妍向他讲土地改革时认真的语气觉得有些好笑,那时他还只是个吃不饱的孩子,听了这话只想着若是能有自己几亩地就好了,不料如今竟然成了要仔细考量改革土地的人了。
原来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第二十八章
元将可用之人不多,能经常取胜的更少,只一个宰相脱脱领着元朝的大部分精兵,哪里有新政权建立便打哪里。他的军事才能不错,在元朝朝廷中也颇有些声望,取得的战绩也都不错。
只不过他遏制住了北方刘福通又要往南方赶着打压徐寿辉,其余镇压起义军的部队大都只是藩王地主的部队,另一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也就是最近才纠结了武装起家的。与离朱元璋千里的脱脱不同,这个汉名李察罕的元将是王保保的舅舅,与王保保二人共同在离滁州不远的地界打压起义军。
此时他们的兵力倒是不多,朱元璋倒是有将他们打败打退的可能,但是他还不想引起元朝朝廷对自己的警惕,否则自己便得面对上元朝的百万大军,实在不值。
于是,他让李善长带着被他俘获的集庆官员以及众多被从府库中搜罗来的财物去了李察罕处。李善长知道他的心思,在李察罕的面前伏低做小极尽卑微之言,只说朱元璋是个在乱世中不得已带着弟兄们博生路的人,如今已经得了富庶的集庆城,只想着好好过日子,不愿与元军再作对,希望李察罕能够体谅。
李察罕也模糊地知道如今朱元璋的兵力,既然朱元璋向他示好,他也就接受了,想着先将那些弱小势力都吞并了,等着朝廷派了大军来再向朱元璋动手。他觉着朱元璋这样一个思想小富即安的人一定是出不了头的,并不着急对付他,何况朱元璋本就低调,倒也不会让他面对朝廷的时候为难自己地盘上又出了一个新政权。
他打着哈哈与李善长说了话,明明是敌人,面上却也还算是其乐融融。
只是双方都知道这只是缓兵之策,一旦李察罕能抽出手来了,朱元璋的集庆城还是会被他攻打的。但具体要多久,等到了时候又会有怎样的胜负就都是未知数了。
就在朱元璋巩固城防,发展农业,鼓励商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滁州在他手下较为平定,滁州附近的城池受的剥削就更重了,又是战火连天,原本是私盐商人的张士诚与其兄弟及相识的其余盐商商贩忍受不了,也发起了起义,迅速夺下了高邮与泰州。
私盐商人本就富裕,他们各处招兵买马收买人心,很快便壮大了起来,竟然在高邮建了国,号大周国,张士诚则自称诚王,以天佑为国号。
李察罕迅速作出反应,与其余只是小打小闹般的起义军不同,一个新的政权是公然与朝廷叫板。为了应对元朝朝廷对他的责难,他停下了对其余起义军的战争,调集他手下的所有兵力攻打张士诚。张士诚自知他手下钱财虽多,士兵却是无法敌过李察罕的,连忙向身在集庆的朱元璋递了求援的信件。
他在信中讲了一堆大道理,只说是世道艰难,起义军之间就该相互扶持着,又说他与朱元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让朱元璋仔细思索。一封信看完,朱元璋暗自觉得好笑。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救援?”他把信件向自己的手下们传递了一遍,没有表达自己的态度,只是问了他们的想法。
“我觉得他信中说的也不无道理,索性咱们练兵也有段日子了,也算是兵强马壮,帮他一把省的元军打完他们转头趁势来打我们。”汤和抢先发言了,他到底还是对这些以白莲教红巾军名号起义的人带点感情,有心想要救一救。朱元璋没有对他的观点发表评论,只转脸向李善长问道“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