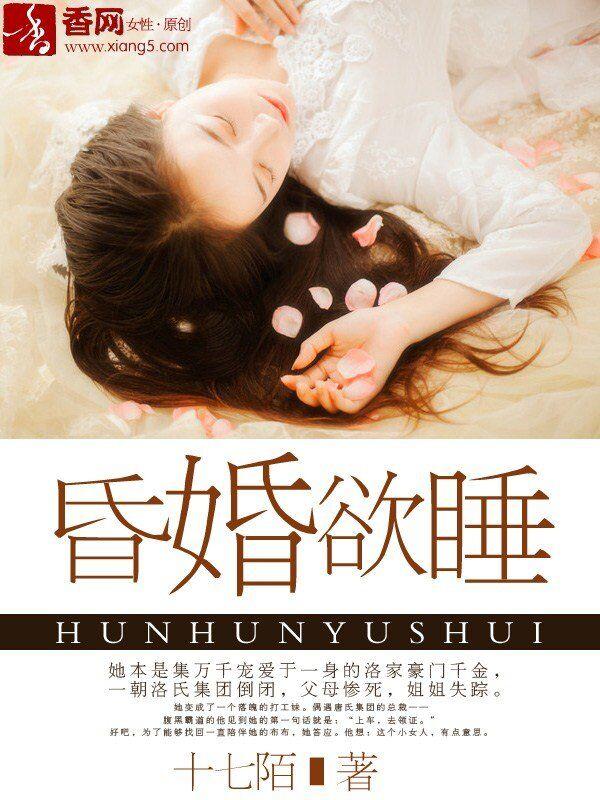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城堡里的男人叫什么 > 第69章(第1页)
第69章(第1页)
是发型师小姐,朱莉安娜明白过来了。往下瞧瞧,她明白自己什么也没穿,那个女人是正确的。
&ldo;乔,&rdo;她说,&ldo;他们不放过我。&rdo;
她找到了床,找到了她的箱子,打开来,倒出了许多衣物。内衣、罩衫,衬衣……一双平跟鞋。
&ldo;让我回来啦,&rdo;她说着又找出一把梳子,麻利地梳了梳头发,再刷了刷,&ldo;什么滋味呀,那个女的就在门外,马上要敲门了。&rdo;她站起身去找镜子,&ldo;这样好些不?&rdo;
镜子在衣橱的门上,她转过身子,扭过头去,踮起脚尖来打量自己,&ldo;我真烦死啦,&rdo;她说着扭头四处找他,&ldo;我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净让我生病,对我没帮助。&rdo;
乔还坐在地板上,紧捂着一边脖子说:&ldo;听着。你好得很。你割破了我的主动脉。脖子上的动脉。&rdo;
她拍着嘴巴,咯咯地傻笑起来:&ldo;哦天呐……你真是个怪人。我是说你满嘴胡言。主动脉在你的胸腔里,你说的是颈动脉。&rdo;
&ldo;如果我随它去,&rdo;他说,&ldo;两分钟内我的血就会流干。你知道的。帮帮我吧,叫个大夫或救护车。你明白我的话吗?你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好的,你去打电话或者去叫个人来。&rdo;
她想了一会儿说:&ldo;我的意思是去。&rdo;
&ldo;好的,&rdo;他说,&ldo;不管怎么样,替我把他们叫来。看在我的面子上。&rdo;
&ldo;你自己去吧。&rdo;
&ldo;我还没完全把伤口捂住,&rdo;她看见血从他的手指间渗出来,顺着手腕流下来,地板上淌了一摊血,&ldo;我不敢动。我得呆在这儿。&rdo;
她穿上了新外套,合上了新买的人工缝制的手提包,拎起了她的箱子,还有那些大包小包,只要拿得下的都拿了,尤其是确信拿了那个装了蓝色意大利时装的大盒子。打开房门时她回头看看他。&ldo;也许我到总台去叫他们,&rdo;她说,&ldo;是在楼下吧。&rdo;
&ldo;好吧。&rdo;他说。
&ldo;行啦,&rdo;她说,&ldo;我会告诉他们。别指望我会回大峡谷城的公寓去,我不会回那儿啦。我有许多德国银行的支票,因此我的经济状况很好,什么也不在乎。再见了,我很抱歉。&rdo;
她关上了门,拎着箱子和尽可能多的大包小包,沿着大厅飞快地离去。
在电梯口,一个上了岁数、衣着考究的商人和他的妻子帮了她一把。他们替她拿了大大小小的盒子,在楼下的大厅里,他们替她把东西交给了一个侍者。
侍者拎着她的箱子和大包小包,穿过大厅,出门到了前廊。她找到一个旅馆雇员,他告诉她如何取回自己的车。不一会儿,她就来到旅馆底下冰冷的水泥车库里,等着侍者把她的车开过来。她在手提包里摸到了零钱,付了侍者小费。接下来,她明白自己要把车开上亮着黄灯的车道,拧亮车灯开上黑漆漆的大街,汇人车流和霓虹灯广告牌之中。
旅馆门口,穿制服的侍者亲自把她的行李放进了车厢,满面真诚的微笑,令人鼓舞,她给了他好些小费,然后驱车而去:没有人拦她,这使她很高兴,他们连眼都没抬一下。我估计他们知道他会结账的,她想,或者在他登记时就已付清了。
在她和别的车一起等红绿灯时,她想起来,她没告诉总台,乔坐在房间的地板上,他需要医生。一直在那儿等着,从现在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直等到清洁工明天的某个时候发现他。我最好回头,她决定,或者打电话。遇到公用电话亭就停车。
当她开着车寻找停车的地方和电话亭时,她想这么做太傻了。谁会料到一小时前的事呢?当我们签约时,我们购物时……我们几乎会继续下去,穿上衣服一道出去吃晚饭,甚至还会出门上夜总会去。她发现自己哭了起来,眼泪从她的鼻尖上淌下来,滴到了她的罩衫上,车在开着。糟糕透了,我没求过神谕,它会让我知晓,给我告诫。我为什么没求神谕呢?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求,旅行的任何地方,甚至在我们离开之前都可以求。
她不由自主地呜咽起来,接着是一种她以前不曾有过的嚎啕大哭,把自己都吓坏了,但她抑制不住,即使咬牙齿也不行。一种可怕的嚎眺,如泣如诉,从她的鼻腔里发出来。
她把车停下来坐在那儿,让发动机轰鸣着,浑身颤抖着,双手放在外套口袋里。
主啊,她凄惨地呼唤道。得啦,我估计是出了那档子事。
她钻出小车,从后厢拽出箱子,在后座上把它打开,在衣服里左翻右找,找出了两册黑封皮的神谕。就在车后座上,马达还在转着,借着商店橱窗里的灯光,她掷出三枚银币。我想要干什么?她求问道。告诉我该去于什么,请吧。
六线形四十二。&ldo;增加&rdo;,移动第二、三、四和最高的线,于是变成了六线形四十三。&ldo;满贯&rdo;。她如饥似渴地翻着文本,心里面捕捉一层层的意思,收集拢来,理解它,基督耶稣啊,它准确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情形‐‐又一个奇迹。所发生的一切,都展现在她的眼前,行动计划,纲要性的。
它促使某个人去从事某件事。
它促使某个人横渡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