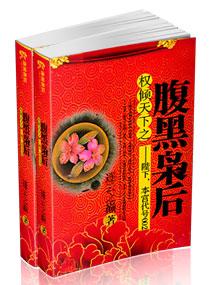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是哪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 第106章(第1页)
第106章(第1页)
终于,当文明到来的时候,真正的装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整个伟大的艺术消亡了。其过渡形式就是‐‐在每一文化中‐‐这样或那样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前者是对早已存在的古代的和无心灵的装饰(规则、定律、类型)的一种滥情,后者则是一种模仿的滥情,不是模仿生命,而是模仿一种更古老的模仿。我们发现,建筑的趣味取代了建筑的风格。绘画的方法与写作的样式主义,不论是采取旧的形式还是新的形式,也不论是出自本土或是来自异邦,都只是随时髦的潮流而此生彼灭。不再有内在的必然性,不再有&ldo;学派&rdo;,因为每个人选择什么和从哪里选择都是随心所欲。艺术变成了工艺,且在所有门类中都是如此:建筑和音乐、诗歌和戏剧;最终,我们具有了一套图绘的和文学的惯用手段,缺乏任何深刻的意义,且依趣味决定其运用。我们面前所具有的,就是装饰的这一最终的或工业的形式‐‐不再是历史的,不再处于&ldo;生成&rdo;的状态‐‐不仅在东方地毯的样式中、在波斯和印度的金工的样式中、在中国瓷器的样式中,而且在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见到的埃及(和巴比伦)艺术中,都是这样。克里特岛的米诺斯艺术是纯粹的工艺品,是埃及的后喜克索趣味在北方的分化物;与之&ldo;同时代的&rdo;希腊化-罗马艺术大约从西庇阿和汉尼拔时代起也同样地服务于追求舒适的习惯和才智的展示。从罗马内尔瓦广场(foruofnerva)的修饰丰富的柱楣到后来西方的地方陶瓷,我们都可追踪到某一不可改变的工艺的稳固的构成,这种构成我们在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同样可以找到,并且我们可以假定在佛陀以后的印度和孔子以后的中国也同样能看到。
五
故而,主教堂和金字塔陵墓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且恰恰是在这些不同中,我们可以把握住浮士德心灵的强有力的现象,它的深度冲动拒绝去与一条道路的原始象征联系在一起,并且从刚刚开始起,它就渴望着超越每一视觉的局限。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伟大的萨克森人,如法兰克尼亚(frannia)和霍亨斯陶芬的皇帝‐‐他们之所以遭致失败,是因为他们无视所有的政治现实,在他们看来,承认任何边界就等于是背叛他们的统治观念‐‐的政治野心更为埃及的国家概念所不容呢?在这里,无穷空间的原始象征及其所有不可言喻的力量,进入了能动的政治生存的领域。除奥托诸帝(theottos)的形象以外,康拉德二世(nrad2)、亨利六世(henry6)和腓特烈二世(frederick2)的形象代表着北欧海盗-诺曼人,他们是俄罗斯、格陵兰、英格兰、西西里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还有伟大的教皇,如格列高里七世(gregory7)和英诺森三世‐‐他们的目标同样是想使他们的可见的影响范围施及整个已知的世界。这正是始终漫游在无限中的圣杯骑士、亚瑟王和西格弗雷德传说的英雄与地理视野上温和得多的荷马的英雄的区别所在;也是把人们从易北河和卢瓦尔河引到已知世界的尽头的十字军与古典心灵借以创作《伊利亚特》的历史事件的区别所在‐‐我们从那一心灵的风格中可以可靠地认定这些事件是局部的、有限的、完全可以理解的。
多立克心灵实现的是具体在场的个别事物的象征,同时还有意地拒绝所有远大的、影响深远的创造,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后迈锡尼的第一个时期才没有给我们的考古学家留下任何东西。这种心灵最后获得的表现,就是多立克神庙及其纯粹外部的效果,它把景观当作是一种块状的意象,但否认并在艺术上看不起内部空间,认为内部空间是一种非存在,根本不可能存在。埃及人的列柱支撑着大厅的屋顶。希腊人借用了那一主题,但赋予了它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意义‐‐使内部建筑类型与外部完全分离。外部的柱廊一定意义上就像是一个被否定的内部的浮雕。相反,麻葛心灵和浮士德心灵是建造高度。当穹顶被置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内部空间之上时‐‐其结构预期分别采用了代数的数学和分析的数学‐‐它们的梦中意象就变得具体了。在从勃艮第和佛兰德斯扩散开来的风格中,肋形拱门及其弦月窗和飞扶壁使围合的空间从包围自身的、可为感官所感知的表面中解放出来了。在麻葛式建筑的内部,&ldo;窗户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构件,还只是一种功用形式,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说得粗率一点,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开孔。&rdo;当窗户实际上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的时候,出于艺术印象的缘故,它们还是被柱廊遮挡着,例如在东方的巴西利卡中。相反,作为建筑的窗户,是浮士德心灵所特有的,是这一心灵的深度经验最重要的象征。在它那里,可以感觉到一种想从内部向无限升腾的意志。同样的意志,也蕴涵在与这些拱门同宗的对位音乐中。首要的是,这种音乐那缥缈无形的世界,曾经是且仍然是哥特式的,甚至当很久以后,复调音乐升至&ldo;马太受难曲&rdo;(atthewpassion)、&ldo;英雄&rdo;(eroica)、&ldo;特里斯坦&rdo;和&ldo;帕西伐尔&rdo;那样的高度的时候,它因为内在必然性而成为了教堂式的,它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十字军时代的石头语言。为了摆脱古典的形体性的一切踪迹,浮士德式的建筑竭尽全力采用了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装饰,这种装饰以其对植物、动物和人做的不可思议的印象变形[莫阿萨克的圣皮埃尔教堂(stpierreoissac)],来抗拒石头的限制力量,它把建筑的所有的线条都融入某一主题的旋律和变调中,把所有的立面都融入多声部的赋格曲中,把其雕塑的所有形体性都融入服饰皱折的音乐中。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我们的教堂窗户的巨大玻璃幕墙以深刻的意义,这些玻璃幕墙上绘有色彩缤纷的、半透明的且因此整个地无形体的绘画‐‐这是西方文化的时空中所独有的一种艺术,与在古典壁画中所能想象到的形式恰好形成最完全的对照。在巴黎的圣礼拜堂(sate-插pelle)中,对形体性的这种摆脱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在那里,石头实际上消失于玻璃的微微鳞光中。而壁画同墙壁合为一体,它就画在墙壁上,且随墙壁一起发展变化,它的颜料作为材料是富有表现力的,在这里,我们运用颜料并不依承荷它的表面而定,而是有如管风琴的音符,在空间中自由地运动,而建筑的形态,也在无穷中保持着平衡。请把这些教堂的浮士德精神‐‐近乎没有墙壁、高耸的穹顶、五彩斑斓的光的漫射、从中殿到唱诗席的升腾‐‐同阿拉伯式的(亦即早期基督教的拜占廷式的)圆顶教堂比较一下。阿拉伯式的穹顶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巴西利卡或八角形主座的上空,它实际上也是对古典建筑在线脚和柱子中所体现出的自然重力原则的胜利;它还是对建筑形体、对&ldo;外部&rdo;的一种抗拒。但是,建筑外部的缺乏本身尤其强调了墙体的未被打断的连贯性,墙体把一切关闭在洞穴中,不容许有任何脱离它的想法和希望。一种巧妙地混合的球面形式与多边体形式的相互渗透;一件重荷如此巧妙地置放在一个石鼓上,以致看起来像是没有重量地悬浮在高空,然而又封闭了内部空间,没有一条出口可寻;所有结构的线条都被隐藏起来;通过圆顶中心部位的一个小开孔照射进来、但仅仅是为了更加突出地强调墙体的封闭性的模糊的光线‐‐这一切便是我们在拉韦纳的圣维塔莱教堂(svitale)、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耶路撒冷的岩顶穹顶寺(dooftherock)这些艺术杰作中所看到的。埃及人把浮雕刻意地放置在平坦的底座上,为的是避免侧面深度的任何比例缩短的暗示,而哥特式建筑师在玻璃上绘画,为的是在没有平坦的底座的空间世界中进行描绘,麻葛式的建筑师则在墙上贴上眩目的、以金黄色为主调的马赛克和阿拉伯图案,因此他是把他的洞穴浸淫在非现实的、童话般的光中,而对于北方人来说,这种光在摩尔人的艺术中也一直具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