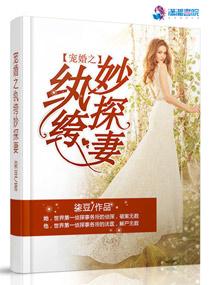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总裁的替身妻第7集免费观看 > 第089章 再一次失去(第1页)
第089章 再一次失去(第1页)
祁舒童轻轻颤抖着,极力压抑着呜咽。
唐砚乔用力将她抱在怀里,心如刀绞。此时此刻,他甚至无法再开口请求她留下这个孩子。他不能这么自私。
她终于忍不住,在他的怀里轻轻抽泣起来。
唐砚乔低头,亲吻着她的额,声音低沉喑哑,却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舒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答应你。如果这个孩子最终和我们无缘,那也不是你的错。”
如果他早知道有一天他会如此爱她,他绝不会让这一切发生,只可惜,他的错误已经无可挽回。
唐砚乔依然记得他们初见的时候。她被律师从拘留所带出来见他,头发凌乱,狼狈至极,可是那双眼睛却异常的沉静,那样的眸子,与其说是认命,不如说是对命运无声的抗争。
她似乎总是这样,看似不声不响,毫无棱角,可实际上,她的内心从未屈服,所以一旦有机会,她就会爆发出如烈火一般的狠绝。
所以当初她面对养父的侵犯,她选择了反抗,就用了最激烈最危险的方式。
所以当她决定不再爱他,她宁愿舍弃一切也要将他割舍。
唐砚乔想,或许就是因为看到她骨子里的不肯屈服,他才会爱上她,可是如今,当她把这份狠绝用到他的身上,却让他痛彻心扉。
不知道过了多久,怀里的女人终于停止了低泣。
她从他的怀里抬起头,却不敢直视他,而是低低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唐砚乔没有说话,而是拿出湿巾来,认真又轻柔的擦拭着她脸上的泪痕。
“我们回去吧。”他什么也没有说,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
“谢谢。”祁舒童感激他的体贴,此时此刻,她真的很害怕他会质问她,既然不舍得,为何还是坚决不肯留下这个孩子。她想,或许他早已洞察一切。
回去的路上依然是长久的沉默,唐砚乔扭头看身边的女人,却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
或许是刚刚哭过一场,她太累了,此刻她蜷缩在座位上,眼睛的红肿甚至未曾褪去,双手依然紧紧的攥着那份检查报告。
男人心中微涩,轻轻的伸手将她揽到怀里,让她靠在自己胸口,祁舒童也本能的伸手抱紧了他。
唐砚乔心中一热,手臂下意识的收紧。他心里清楚,或许像这样的机会,已经很少很少了。
所以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唐砚乔异常的恼火。只是看到显示的名字,他略一蹙眉,终究还是接起。
十分钟后,车子在一处广场停下,唐砚乔小心的移开祁舒童的双手,将她放在座位上,确信她依然安睡,他才放心的下了车。
不远处等待着他的人,正是聂泽芜。
唐砚乔关上车门,朝他走去。
“聂先生。”他淡淡的开口,“听说你要离开A市?”
聂泽芜笑了一声:“唐先生果然消息灵通。没错,既然这边的事已经走上了正轨,我就没有待在这里的必要了,家父召我回去。只是,临行前还有一些事需要和唐先生谈一谈。时间仓促,就约在这里,还请唐先生不要见怪。”
“当然不会。”唐砚乔挑了挑眉,“不知道聂先生有什么事要和我谈?”
唐砚乔心中清楚,虽然这个男人知道唐陈惠的事,但如果他真的是个聪明人,就不至于拿这件事来威胁他。别说聂泽芜自己此时深陷晏家内斗急需盟友,在这个时候和唐家为敌有多不明智,就说这件事本身,也不见得能给唐家带来多大的伤害,聂泽芜如果想用这个把柄获取好处,恐怕也根本得不到什么。
所以唐砚乔丝毫不担心这件事。相反,如果聂泽芜真的拿唐陈惠说事,只能说明他根本不足为虑。
果然,聂泽芜略带忧郁的叹了口气:“我苦追唐小姐多时,她却始终不肯对我敞开心扉,我只能遗憾作罢。只可惜没有时间跟她道别,还请唐先生代我跟她说一声抱歉。”
唐砚乔目光微沉,轻轻点头:“是舍妹无福。”
聂泽芜半开玩笑的说:“只可惜唐先生似乎只有这一个妹妹。不能与唐先生结为秦晋之好,我实在不甘心。”
唐砚乔闻弦歌而知雅意,微微一笑:“就算不结成秦晋之好,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做朋友。聂先生为人,我都看在眼里,我很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这是我的荣幸。”聂泽芜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伸出手来,“唐先生,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