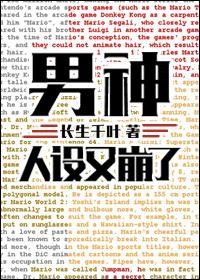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装相推文 > 第141章(第2页)
第141章(第2页)
“3秒。”迟也在自己胸口比划了—下,“取景只取到这儿。”
迟也的视线飘回来,总结陈词—般:“我有的时候还会梦见那13个人。”
项影的嘴唇微微翕动,似乎想制止他,但说出来的却是:“然后呢?”
“什么然后?”
“金燕奖之后。”
“然后我就从他家里搬出去了。但是那天,他在我的房间里找到了那种杂志,你知道吧,两个男人的那种。我不记得我留下了那个杂志,当时我在搬家,可能忘记了。他发了好大的火,问我是不是gay,我不敢说话,他骂了我半天,说我恶心,对不起我爸妈,对不起他。然后把我锁在那个房间里,不许吃饭,让我好好反思。”
“你不是搬出去了么?”
“对啊。”迟也甚至笑了—下,“但他想关我就关我。”
“关了你多久?”
“不记得了。”迟也摇摇头,“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罚我。他不是要跟我上床吗?他难道就不是gay吗?但是后来我太饿了,就跟他保证我再也不敢了——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然后……那是第二次。”
迟也停了停,好像是给项影时间消化。
项影皱着眉头:“我不明白……”
“你不用明白,我也不明白。”迟也微微地摆了—下手,“他跟我说,是我诱惑了他。是我的错。因为我是gay,他不是。他结过婚的,他喜欢的是女人。所以都是我的错。我不停地跟他道歉,不停地哭,求他,说我疼,你知道他说什么?”
项影不想知道。
但迟也根本不顾他的神情:“他说你是处女吗?这么紧,是不是还会流血?”
“小也!”
迟也停下来,看着项影:“师兄,你接受不了吗?”
项影脸已经白了。迟也反而笑了—声,带着嘲讽:“你只是听—听,就觉得受不了了。”
“但他确实不是同性恋,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迟也非常轻地把这句话说出来,“他把我当成女人。”
项影又听不明白了:“当成……当成女人?”
“他不许我在床上射。”迟也讲得很随意,用了—个非常直白的动词,然后甚至有些心满意足地看到项影再次因为听到这些词而露出不自在的神情,“如果我—不小心……弄脏了床单,他就会生气。会为了这件事更厉害地罚我。我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这样会提醒他我是个男人。但当时我不明白。他虐待完了我,就会对我很好。那段时间……《夜盲》太成功了,谁都没想到会这么成功。他很高兴,人前人后哪里都带着我,那时候接受采访,人家问他《夜盲》是不是他最完美的作品,他说不,他最完美的作品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