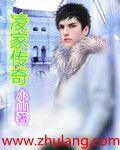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簪花少年郎 > 第200章(第1页)
第200章(第1页)
“我,也不知道。不若这样,我这就进城去问问。”,他有些抱歉地说。
谢奚见他浑身疲倦,摆摆手:“算了,等我有空了再去问问,这几日辛苦你了。”
五书笑说:“不敢当,庄主今年的收成大好。”
谢奚叹气:“有什么用?我收成好了,税也加大了,我倒是还好,其他人可就惨了。”
结果晚上崔邺就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姚重和几个年轻人。
崔邺进门就说:“准备些好酒,今日要大醉一场。”
姚重忙推辞:“柬之不可。”
谢奚不做他想,放下笔,让吴媪去准备了,她自己则在旁边的实验室里研究新种的胚芽。
一直到午夜时分,家里的人都睡了,隐隐约约能听见远处的狗吠声,才见崔邺推门进来。
谢奚屋里的灯还亮着,她人趴在桌上睡着了。
崔邺没醉,姚重和这几个人,自小在京里长大,喝的是上好的梨花白,甘醇浓香,不似他学喝酒开始喝的就是西北的烧刀子烈酒,所以这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把人灌到趴下,他自己都毫发无伤。安顿好几位才出来。
进门见谢奚趴在桌上,心里又心疼,又无奈。
走近刚抱起她,谢奚就醒了,闻到酒味,迷迷糊糊问:“你喝了多少?”
崔邺自己也能闻到烈酒的味道,笑说:“喝了不少,你睡吧。”
谢奚被惊醒了,睁开眼,被他抱着放在炕上,笑说:“快睡吧,待会儿天就亮了。”
崔邺脱了外衫躺在她身边,谢奚也不嫌弃他,将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上。
崔邺自己说:“姚重被点了将,去南地平叛,他是忠君之臣,这次去了凶多吉少。”
谢奚问:“为什么?”
“你不清楚朝中的事情,反王是前朝宗室,手里的将都是前朝镇守西南边境的悍将,朝中根本就没有与之一战的对手。当年也不过是路途遥远,招降安抚为主。如今天下不太平,可不是当年的情形了。”
谢奚问:“那你父亲若是对战,可有胜算?”
崔邺笑笑,暗中抓着她的收,说:“不知道。我没有真正的见识过他的本事。”
谢奚问:“今年的夏税涨了一倍,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