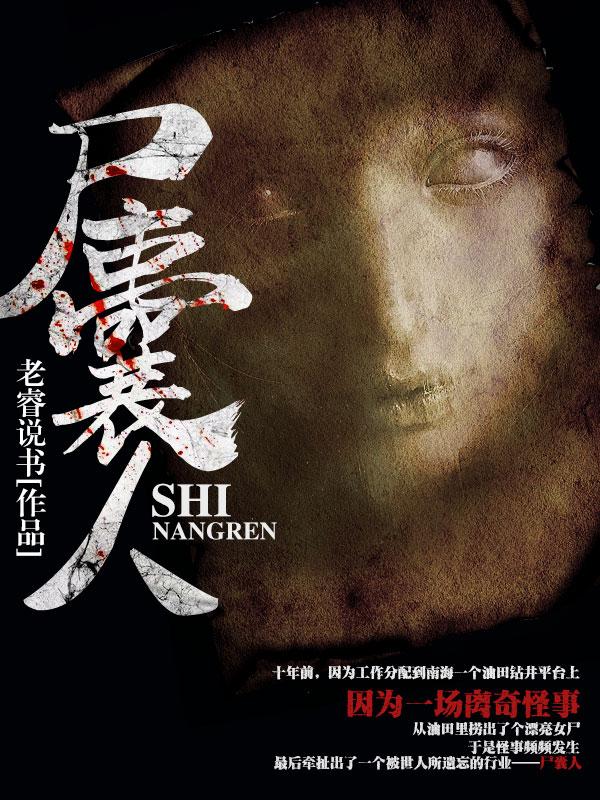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公主艳煞越十方无防盗 > 第270章(第1页)
第270章(第1页)
姬珧一听,心中疑惑更加大了。
他像是在提醒玉琅风,不要多事也不要挑事。
玉琅风坐下去,两腿一伸,浑不在意道:“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怎么算给玉家丢脸?有的人做得我说不得,这又是什么道理?”
玉睿丞怔了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他刚要说话,姬珧也走了过去,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坐下,转头看着他,轻笑一声:“阁下意思是,刚才你说的话都是事实?”
玉琅风舔了舔牙冠,反问:“难道不是?”
“本宫只是有些好奇,本宫既为大禹长公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玉无阶虽为玉家家主,在本宫眼里亦为臣民,他为本宫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有什么不对吗?”
玉琅风没想到她会这么伶牙俐齿,张口欲说,又顿了顿,脸上重新换上笑意:“当然没什么不对,只不过君君臣臣,谁追随谁效忠谁这种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说不定到时候身份转变,跌落泥潭,失去那层光鲜亮丽的身份,就什么都不是。”
“琅风!你住口!”玉睿丞厉声呵斥,随后赶紧转身给姬珧赔不是,“殿下莫要过心,琅风乃是我们同辈之中最小的那个,多少有点顽劣,目中无人不懂礼数,如果有哪里得罪了殿下,还请殿下不要怪罪。”
玉无阶走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玉琅风:“若你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便去玉家宗祠里跪个三天三夜,好好想想自己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
玉琅风见他拿宗祠来压他,瞬间也沉下脸来,从椅子上站起,可一看玉无阶和玉睿丞都是将矛头指向他,脸色几经变换,最后微微一笑:“家主和大哥别生小弟的气,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罢了,何况公主殿下还在这里,我怎么敢真心对殿下不敬。”
玉琅风变脸跟翻书一样快,姬珧却没怎么惊讶。
她来沅州之前对玉家也有些了解,在玉无阶没回玉家之前,玉家家主一直都是他堂兄玉睿丞担当,他们这一代直系子弟有一十三个,其中最小的玉琅风从小就瑶林玉树聪明过人,却因为性格乖张怪异为人不喜,始终无法赢得家族认可,与家主之位无缘。
也因此,他对玉睿丞和玉无阶心中都有怨气。
只是玉家家大业大,仅家主一人无法治下,所以除家主之外,同辈子弟亦有话事权,并非是家主一言堂。
玉琅风敢如此嚣张,背后也有支持他的三房势力,如不是犯了大事,为了一族和谐,玉无阶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只是姬珧可不是玉家人,她没道理惯着这人的臭脾气,她淡淡笑了笑,笑里藏着刀:“还好你只是说玩笑话,不然就不止是宗祠罚跪那么简单了,可怜金宁卫的刀剑很久都没机会出鞘,如果你觉得自己活腻歪了,本宫倒是不介意帮帮你。”
玉琅风眼中满是防备,冷冷地看着她,末了垂下视线,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殿下何必跟我这个无名小辈过不去,刚才是我冒犯了,我赔罪。”
说罢,他躬着身子作了一揖,又抬头看向姬珧,眼里有抹意味不明的玩味:“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沅州,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周游一番,沅州美景天下绝,殿下一定会大饱眼福流连忘返的。”
姬珧留意他的语气,总感觉他怀里有话。
夜里,她与玉无阶独处时,忍不住嘲笑他:“你身为玉家家主,为何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一个小小的堂弟也敢欺负到你头上。”
哑奴给她布茶,姬珧捧在手心里晾着,一边吹着气一边留意玉无阶的神色,后者眉头紧锁,不假思索地想着什么,随口道:“我一直都在金宁,很少回玉家,我不在时,族中事物多交给大哥打理,他之前是家主,其实比我更熟悉族务。不过,今日确实奇怪……”
姬珧放下茶杯:“怎么?”
玉无阶摇了摇头:“十三郎以前也经常是那副狂妄自大的模样,与我不善,也常常挑衅大哥,但他只是心性如此,绝不是没脑子,今日的事,他没必要这么愚蠢惹你生气,而且一点也没把你放在眼里。”
茶放凉了,姬珧端起来要喝,眼前突然伸出来一只手,盖在茶杯上,她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哑奴,哑奴似乎也有些错愕,惊惶之下就将手拿开了,赶紧告罪。
姬珧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回过头看着玉无阶,继续刚才的话题:“他背后是有什么倚仗吗?”
“不知道,”玉无阶没留意他们二人之间的小插曲,而是眉头紧锁,半晌后抬眸看她,眼里有几分凝重和认真,“你想要玉家着手生产那批火器,在此之前就必须保证玉家忠心于你。十三郎态度对你这般轻慢,绝对有猫腻,在此事调查出来之前,图纸的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姬珧知道急不得,不止是玉家如此,如今整个大禹势力盘根错节,单靠金宁卫和积室山陈旧的情报网,无法准确地确定一个人现在站在哪边,又是什么立场。
她在玉家一住就是一个月,期间她命金宁卫把黑狼山玄铁矿整个翻过来彻查了一遍,在这期间,她也发现玉家明显分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方对她恭敬有礼,一方对她不屑怠慢。
四月十五,姬珧接到宣承弈的密信,围困月柔的烈火罗大军不知不觉减少了许多人,去处不明,他担心生变,提醒姬珧警惕,姬珧赶紧去信云城,让裴家盯紧了烈火罗的动向,切不可放过任何一个外族人越入边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