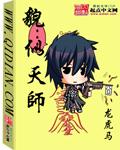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引火汤的标准配方 > 第87章(第2页)
第87章(第2页)
贺南枝就被投喂了一堆小零食,隔几分钟就有个小护士过来嘘寒问暖,顺便给她塞个糖果吃。
唇间弥漫着甜度超标的糖味,也让她今晚绷紧的神经稍微得到缓解。
她视线,也不知不觉地透过半掩的门,落回了谢忱岸身上。
清冷冷的灯光照映着室内墙壁,显得空间有些空旷安静,护士已经将谢忱岸的手臂裹上了白色绷带,如同玉雕分明的骨线被缠绕上几圈,血迹也擦拭得干干净净,透着难以言词的矜贵感。
视线再往上。
看到他的脸,贺南枝有些恍惚地回忆起,谢忱岸年少时第一次受伤住院,好像是拜她跟谢忱时所赐。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她真信以为真要出人命了。
柔软的小手抱着纤细膝盖坐在医院后花园的阶梯上,睫毛低垂,剔透的泪珠一颗颗往下坠,小声地念念碎着身边模样清隽的白衣少年:“那小混混入室偷小狗,手上有凶器……我们该躲起来等警察叔叔来的,怎么办,谢忱岸脑袋替我们挨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躲什么,那笨蛋狗都快被勒死了。”白衣少年一直懒洋洋地跟着她蹲在外面,声音冷淡又气闷:“别哭了,你有一群小竹马呢,死了个而已。”
贺南枝抬起湿漉漉的小脸蛋,被整得欲哭无泪起来:“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啊谢忱时,终于要能成为你爸爸的独生子了。”
谢忱时略顿了下,语调越发懒散下来:“你天亮再恭喜我。”
“有区别吗?”
“医生说谢忱岸活不过今晚了。”
路灯下的初雪仿佛停了瞬,贺南枝张了张小嘴,有些茫然又带着不可置信,忍了几秒,没忍住,眼尾的泪珠蓦然砸了下来,生猛地都能水淹了这家医院:“呜呜呜我后悔了,以后我再也不跟你一起搞竹马小团体孤立谢忱岸了,他好可怜,一直被我们联手排挤……呜呜谢伯伯最优秀的儿子没了,我爸爸又没儿子,不知道能不能拿贺斯梵赔给谢家。”
应景似的。
贺斯梵冷漠至极的嗓音忽然从身后传来:“鬼哭狼嚎什么。”
贺南枝和谢忱时齐齐地转过头。
看到他说:“进来。”
谢忱时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做派,贺南枝怕到小肩膀都在颤抖,指尖揪着衣角,跟小蜗牛似的,慢慢地往那病房移,她没有继续哭得歇斯底里着了,但是乌黑的大眼睛里满是水雾,看什么感觉都是晃的。
就这短暂的几秒内,贺南枝都想好将来葬礼上该怎么跟谢忱时抱团哭鼻子了。
谁知,刚进去。
她抽泣的哭声卡在喉咙里,先一步看到谢忱岸穿着干净清新的病服靠在枕头前,额头的伤已经包扎好了,绷带莫名衬得他脸侧如窗外初雪般苍白,薄唇血色缺失,许是预测到了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