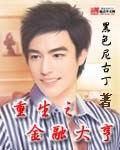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道是无晴却有晴的隐喻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他藉着那火光,也看了周围。这是间二丈见方,一丈多高的小室,砖块密砌,毫不透风。一面墙上,悬着一只龙头,也不知作何之用。
她也注意到了那龙头,心上不祥顿生。她皱眉,道:&ldo;难道是……&rdo;
她的话还未出口,就听那龙头发出&ldo;咔咔&rdo;之响,随即,一柱水流从龙头中喷涌而出。
&ldo;我就知道!&rdo;她愤然道,&ldo;可恶!等我出去要你好看!&rdo;她说罢,用手抚着墙壁摸索,试图寻找脱离的方法。
水流汩汩,片刻间就没过了鞋面,沁出微凉。他低头,静静看着那水面上升,迟迟没有举动。
&ldo;喂。&rdo;她对他的安静万分不满,没好气地开口喊了他一声。
即便这不是什么指名道姓的呼唤,但在这斗室之中,她还能叫谁呢。他抬起头来看着她,依旧沉默,只等着她说话。
火折的微光映照,让她紧蹙的眉间染着深浓的阴影。她走到他面前,道:&ldo;联手离开这里,咱们再打,如何?&rdo;
他不回答,也不举动。
&ldo;你是哑巴么?&rdo;她问出这句话时,并无恶意,只有身陷机关的困窘,以及命在旦夕的紧张。她想了想,又道,&ldo;贤益山庄附近并无江河,只有后院一处池塘,这些水必然来自那里。只要卸下龙头,弄出缺口,循着水流就一定能出去。&rdo;
她一边说,一边看他的表情。黑巾蒙面的他,唯有一双眼睛可以辨视。而那双眼睛里,始终没有可以察觉的情绪。如此情势之下,他的冷静和淡然,透着些许可怕的意味……
她明白了几分,冷哼了一声,道:&ldo;你想死是你的事,我可还没活够呢!不帮忙也罢,别添乱就是!匕首给我!&rdo;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向他伸出了手。
他略微迟疑,还是将匕首交给了她。
她接过匕首后,刻意避开水流,走到了龙头斜下方。这龙头悬在离地八尺来高的地方,她踮着脚尖,伸直手臂,才能勉强够到。她反握着匕首,开始凿龙头旁的砖石。匕首虽锋利,但砖石坚硬,她的姿势又不好使力,凿了许久,不过弄出几道浅痕。但她并未放弃,依旧维持着那个吃力的姿势,一下一下地凿着砖石。
渐渐地,水面已然高至膝盖,她也累了,停下了手,靠着墙喘气。她顺过气息,又转头对他道:&ldo;剑也给我。&rdo;
他不明白为何她还不放弃,&ldo;贪生&rdo;又如何?如此密室,天下谁人能够逃脱?他握剑的手紧了紧,而后,做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决定:他收了剑,从怀中取出了一副精铁指虎,一边套上右手,一边走向了她。
她一眼看到他手上的东西,不满地道:&ldo;有这个你早说呀!&rdo;
他并无一语,在龙头下站定,提劲一跃,攀上了龙头。他略微将身子拉高,而后聚力出拳。指虎与砖墙相击,起一声沉闷之响,方才她苦苦凿击的砖石应声裂开。他稍做停顿,复又聚力,再次出拳。
眼看他如此,她忙开口道:&ldo;够了!你先下来。&rdo;
他闻言,收了拳,松开了攀着龙头的手。落地时,一片水花激起,惹她躲开老远。她确认自己未被沾湿,才又走了过去。到他身边时,她皱着眉头,嘲讽他道:&ldo;手不疼么?&rdo;
疼。当然疼。方才出拳,他用尽全力。指虎虽是精铁所制,但使用者到底是血肉之躯。此刻,他的整条手臂都如同被折断了一般,刺痛入骨。但他却依旧冷然,甚至连眉头都不曾皱起。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疼也好,不疼也好,都没有任何意义。
&ldo;真怀疑你是不是活人……&rdo;她一边嘟哝,一边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火药囊来。她将火折子咬在了口中,学着他的样子攀上龙头。她看了看那被击碎的砖石,用手指抠出碎片,弄出一个三四寸大小的洞来。她扯下一片衣衫,一半垫入洞内,一半留在外头。接着,她将火药囊里的东西撒在了里头,用火折点燃了那半截布料。做完这些,她飞快地跳下来,拉起他躲到了最远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