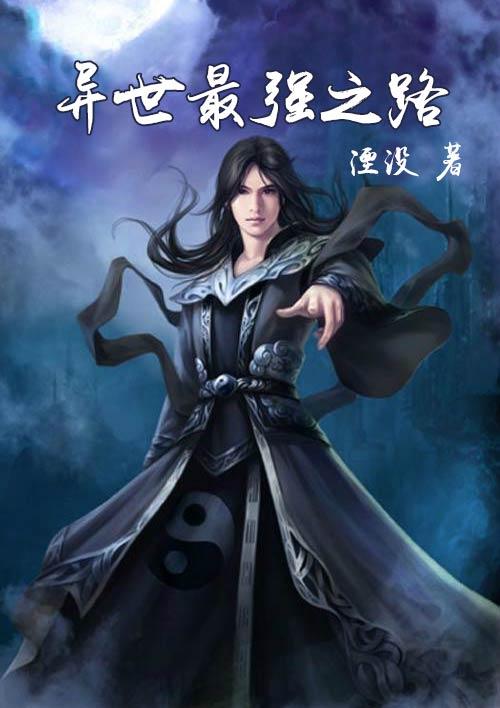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陛下难当宋昭昭笔趣阁 > 第73章 为殿下而来(第3页)
第73章 为殿下而来(第3页)
刘遏沉冷地看着他。
贺启六的笑容缓缓收敛,随即起身来,一下半跪行礼。“贺某,必不负殿下所托。但倘若之后,我及我子孙治理不好这天下,那么这天下,还归殿下并这大郑后人之手。”
“好。”
直到后半夜,宴席将散的时候,篝火的火意也惺忪淡了。将士们喝得半醉,刘遏抱着酒坛起身来,踉跄往营帐中走去。
他不知为何一腔孤寂,像是已经孤寂许久,想听听其他的人声,却想不起还有何人。靡靡乡音,吹彻寒笙,尽都淡去。
刘遏缓缓走着,对上那轮孤寂寒秋的月头,一下撞入人怀中,盔甲半硬,嗑得脸疼。
“殿下,你醉了。”
他拧起眉头,摸向面前那人,摸上那人眉眼,却记不清那人名姓了。怀中的酒坛子随之被人接过,放在一旁。
“你是何人?”
“属下是……周朗。”
“那么周朗,陪孤说说话吧。”
他径自摇晃着,走入帐中。
周朗微愣,跟着他走入帐中。
于是沉重的盔甲被一件件卸下,面上的血痕被人用热的长巾轻柔抹去,就像从前怎样在草屋伺候一般,周朗仍是这样伺候刘遏。
而刘遏躺在被褥上,神情迷瞪。面前的人几分熟悉,他却想不起来。
“你就是那个,在城楼上救下孤的侍卫吗?”
正在洗长巾的周朗闻言神情一黯,“是,是属下。”
“你也来军中了啊。”
“是的,为殿下而来。”
刘遏痴痴看着,烛火晃得头晕,周朗又走过来,轻轻熄灭了旁边的蜡烛,只要刘遏的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做。
于是一切都昏暗起来了。
半醉的刘遏就伸手一扯,将他扯得低下身来。“孤想起你来了。”
“嗯?”
“你是那个,一直在草屋陪着孤的侍卫?”
周朗笑了。“是的。”
“那孤记得你,”刘遏喃喃道,“睡着的时候,会喊孤的名字。”
“殿下……”
“对,就是像这样。”
黑暗里,刘遏又翻过身去,他侧躺背对着周朗,恍惚间记忆不断远去。
一点点月头西斜,他逐渐睡得昏沉。
而同是在黑暗中,屈膝跪上榻的周朗眼神幽暗,指腹缓缓摩挲过刘遏的面庞,直至唇瓣。
“嗯……”刘遏感觉到异物入唇,眉头微微皱起。
周朗俯身来,指尖湿润着,他低低唤道:“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