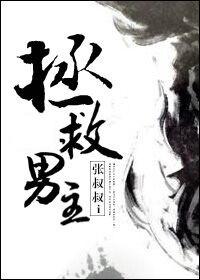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漂亮宝贝和不会爱先生完结了吗 > 第108章(第1页)
第108章(第1页)
只要宝贝跟他解释,他就相信。
“宝宝,别再故意拿话刺我了。”
秦濯态度软下来,抵着宝贝的额头,鼻尖轻轻蹭过他的脸颊,克制着心底的猛兽问:“你和喻肆,到底是什么关系?”
阮乔感受不到秦濯以为的温柔,他只知道自己被强硬地束缚在床上,在刚刚过去的昨晚又被监视者偷拍了照片。
他心底冰凉一片,但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阮乔近乎麻木地问:“你先告诉我,杨杰被人肉的信息,是不是你放出去的?”
秦濯脸色蓦地一变,比起被质问的薄怒,他更觉心脏被人狠狠扼住。
那天离开时阮阮说不许他动杨杰,他违背一向做事的规则答应了,纵着他的小菩萨。
他答应阮阮的事就会做到,可是阮阮竟然不信他。
他相信任何一个室友,唯独不信他。
“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还需要问我吗?”
秦濯语气生冷,平静的表象下野兽正在和禁锢的铁索角力,他应该在失控前就让阮阮走的,但他没有。
近乎默认的回答让阮乔崩溃:“秦濯,我不是说过你不要再参与我的事了吗?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
秦濯总是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做一些偏激的事,酒会上那句“当婊子还要立牌坊”一直在折磨着阮乔,他得了秦濯的恩惠,被秦濯帮助,所以他连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立场说,只要说了就是不识好歹。
“我求求你了,离我远一点可以吗?”
秦濯不自觉加大了掌下的力度,那么单薄的肩头,为什么总是这样倔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张总是甜甜软软叫他名字的嘴巴不见了,说出的话一句比一句扎心。
这是他的宝贝,他怎么可能离远一点,离远了拱手让人吗?休想!他秦濯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
。
“嗯!”阮乔唇上一痛,秦濯掐着他的下巴,狠狠封上了他的唇。
这种任意施为的惩罚,让阮乔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抓起来亵玩的宠物,无比屈辱。
他用力挣扎,水手服的领口被扯开,露出大片洁白的肩颈,秦濯的身体顿时僵住。下一刻,锁骨上传来被大力揉搓的疼,阮乔痛得流出眼泪看向秦濯。
“这是什么?”秦濯冷声问。
锁骨上那片像吻痕一样的红泛上他眼底,那么刺目。而在另一侧,竟然还有一个半消的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