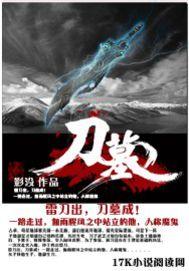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卦卦不得生原文 > 第12章 文 那你还爱谁(第2页)
第12章 文 那你还爱谁(第2页)
她已经记不清。
直至声音消失,才停。
随即,褚清思微微皱起一双眉眼,痛苦到弯下薄弱挺直的细腰,堆在翘头履之上的裥裙也因她身体的屈折而垂落在地,沾染尘土。
她艰难行走几步,将柏木枝靠着树干放下,后以薄背倚靠高树而缓缓屈膝,蹲跪在地上,然后小心谨慎的脱下双足所穿的履。
血将丝绢所制的足衣与足底粘连。
那根树枝上,被手掌所握之处也有淡淡的血迹。
褚清思轻轻将足衣往外扯了扯,血肉分离时,痛感也在顷刻间冲击头颅,而后化为水珠从眼中流出,长睫因此被洇湿。
少焉,擦掉眼泪。
又重新穿上。
她心中明白,经过前面的意外,自己已经彻底迷失方向,这次奔走也将她最后的体力消耗殆尽。
但危机始终未曾离开。
必须随时预备逃。
*
骑行数里以后,男子轻拉手中缰绳。
马扬起前蹄,嘶鸣一声。
最后驯服的在原地缓慢打转。
跟随在男子身后的侍从不解其意,一路走来都不见女子,且毫无任何有人徒步的痕迹,虽然心中觉得褚小娘子不在此处,但也未敢直言:“郎君,可还要继续往前?”
李闻道单手握住缰绳,右手从腰间拔出剑,朝身下轻轻一挑,轻纱瞬间落于掌中。
是女子的披昂。
从黄鹿泽的北方一路走至这里,足有数十里,再经烈日曝晒,无水源能解渴,绝无力气再行。
最多能再徒十里。
他收剑归鞘,冷声命令:“以此为中央,向四周搜寻。”
*
及至黄昏时分,眼中所见的一切都被蒙上落日余晖。
褚清思依然还蹲坐在原地,蜷缩着身体,因即将入夜,太阳与炽热一同离开,惟剩严寒。
她抱着双膝开始忍不住的战栗,茫然的往四周看去。
长兄随阿爷好狩猎,因而家中置有许多舆图。
其中就有一张洛阳的羊皮舆图。
褚清思少时曾经看过,她记得黄鹿泽的西北方向连接着邙山山脉,所以已经不能再继续走。
因为邙山有猛兽,太宗昔年就常去此地狩猎,它比黄鹿泽更危险。
而黄河、洛水就距此在数十里之外。
深夜水汽会更大,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