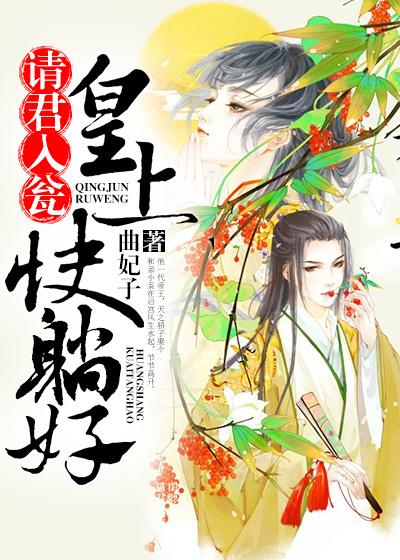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什么臣当道 > 第254页(第1页)
第254页(第1页)
万绍祺原本便是想着如何能将汪自明从那事儿中脱身,听见他现在的话自然也知道,汪自明其实只是不愿自己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他拍了拍汪自明的肩膀,郑重其事道:“我一定会努力帮你的。”只这么一句,汪自明就知道自己没有交错这个朋友,也不再回话,只是笑了一下。虽说是照例上朝,但是最近南朝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原本上朝也不过是走个流程罢了,于是季越的大多数注意都落在了童怜身上。童怜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让季越不由怀疑是不是哪儿没歇好,或是身子又有所不适了,需不需要下朝后让太医去给他瞧瞧。“陛下,臣有事启奏。”百官之间,汪自明往中间走了一步。听见了汪自明的声音,季越这才将注意力从童怜身上挪开片刻,转而看向了汪自明。他记得汪自明是驻守南朝与西域通商路的将军,除非有万般要紧的事情应是不能擅自离守的。自己前两日并没有收到他要回京的消息,眼下看来怕是西域十三国那边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儿。季越:“汪将军突然回京,是西域十三国那边出了什么事情么?”“正是。”汪自明深吸了口气,随后“噗通”一声跪在了大殿之上。这一下除去先前知情的那几个官员之外,所有人都被他吓到了。季越见状不禁蹙眉:“汪爱卿这是何意?”“陛下,四日前,通商路上突然发生暴乱。当日西域十三国的一个王子随商队行至我军驻扎之地,不知从何处突然蹿出了几个南朝人,举刀挟持了西域王子。微臣当时虽已竭力相保,可那些人却不知受了何人指使,在临死前突然掏出一把匕首,刺入了西域王子的大腿。”“待局面稳定,军医前去替西域王子看伤时才发现,那些贼人竟是在匕首上涂抹了剧毒,西域王子已然没了气息……”将所有的事情说完,汪自明以额垂地,大喊道,“臣罪该万死!”汪自明说完,金銮殿上一片寂静,见状万绍祺立刻出列为好友求情:“陛下,此事之中疑云颇多,还请陛下明鉴!”“童爱卿你怎么看。”季越深吸了口气,转而问。童怜听见季越的话,出列弯腰道:“微臣的想法与方大人大抵相同。西域十三国与我朝通商数载,因而有汪将军坐镇一直没出什么大事。微臣相信以汪将军的能耐,不可能轻易让贼人得逞,其中必有我们所不知的事情。”童怜说得不错,只是还没等季越开口,另一个官员便立即站了出来:“陛下!现在重要的是,对于此事西域十三国那边如何看待?西域王子是死在我朝驻军面前的,就算如掌印所言期间还有我们不得而知的缘由,可汪将军出了纰漏,有可能导致我朝与西域十三国友好破裂也是不争的事实。”“钟大人所言未免有失偏颇。”季青和开口道,“现在最重要的应是给西域十三国一个交代,钟大人所说是想陛下不问缘由直接处决了汪将军么?”钟永晏见自己的意思被季青和误解,气得连脖子涨红了:“王爷何必曲解臣的意思,臣不过是觉得此事终究是汪将军的纰漏。若是陛下对汪将军无一点惩处,这往后又会有多少人觉得出错并无大碍,长此以往,律法何存!”汪自明一听,也觉得钟永晏言之有理,丝毫不觉得他有什么言外之意,当即跪拜道:“此事皆由臣疏忽而起,微臣愿意接受一切惩处!”万绍祺哪儿见过汪自明这么老实、抢着要帝王治他罪的人啊,急忙开口说:“还请陛下三思!”“够了。”眼见着台阶下的官员又要吵起来,季越不悦道,“如掌印所言那般,此事中疑云颇多。又因为要给西域十三国一个交代,所以才不能随意了事。汪自明,那些突然蹿出的贼人你可调查过了?”汪自明:“回陛下事出之后微臣便命人调查过,只是那些人本就是在通商路上乞讨的孤儿,微臣并没有查到有什么能用的消息。”闻言,季越的眉头皱地更紧了,他问:“乞儿?若只是些乞儿他们又怎么可能突然暴乱?这期间必有隐情!”季越说着沉默了会儿,最终开口道,“大理寺卿可在?”被叫到名字的大理寺卿上前两步道:“微臣在。”“朕派你明日与汪将军一并离京,彻查此事,你可有异议?”季越说。要知道大理寺卿今年已经年近花甲,此事既是事关重大,又如何可能慢悠悠地前往?可若是走得太快,大理寺卿能不能或者赶到通商路都不一定。大致明白了季越在打什么主意,凌白自然不可能在原地站着,当即出列道:“陛下,齐大人年岁已高,怕是一路多有不便,微臣自请前往。”作者有话说:我:我今天不想写文表妹:还是劝你写一点(因为家里有人阳了,外加我现在有点喉咙不舒服外加咳嗽,感觉随时可能会爆发)交代下朝后,凌白见着童怜,无奈道:“原先还以为陛下最先下手的应是长珩,却没想到竟是我先离了原来的位置。”其实在上朝时听见季越的命令,童怜并没有任何不悦之情,甚至稍稍有些庆幸——还好季越不会因为一时的感情失了偏颇。即使是站在他对立面的童怜,也不得不承认季越这一手下得属实好。西域王子在南朝驻军前被南朝人杀死,这事既然是已经发生了,那无论如何南朝也必须给西域十三国一个交代。而派遣去的官员人选,某种程度上便是南朝对此事的态度。按理来说自然是派大理寺卿前去最为妥帖,但是大理寺卿年事已高,属实不适合在外奔波。于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凌白这个刚刚官复原职的大理寺少卿自然首当其冲。凌白突然说:“童大人这两日是怎么了?而且陛下他……”凌白的话点到即止,但却也足够童怜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了。童怜微微摇头,说:“一些私事罢了。”听完童怜的话,凌白也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四处张望了一番,见没什么人朝他们这儿看,这才松了口气凑到童怜耳边轻声道:“童大人,我先前瞧陛下的模样,应是喜欢你的。”像是担心自己的表达并不准确,凌白稍停顿了会儿,补充道:“我的意思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喜欢。”闻言,童怜不自觉皱眉:“世卿,你怎么……”凌白叹了口气,略带无奈道:“当时你入宫时我便觉得奇怪,再加之陛下看你的眼神,若是再不收敛点,怕是满朝文武都要知道他的心思了。”说着凌白也意识到了先前童怜的话,反问:“听童大人的意思,你应是也知晓了?”童怜听后只是皱眉,将话题一转开口道:“陛下尚且年少轻狂,怕是因为我是与他自小一起长大的,这才不小心将依赖当做了情爱。我南朝的君王又怎可能不娶妻生子,同……同我这个阉人在一起?”听着童怜自轻自贱的话,凌白不禁皱眉。只是他也知自己说服不了童怜,于是也就不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了。他说:“明日我便要离京了,今日难道童大人不应该请我吃顿饭当践行宴么?”听出凌白是为了自己调整情绪才这么说的,童怜自然也不会辜负了他的好意,笑着说:“好,那就如凌大人所言,我们去客栈吃一顿。”凌白不禁感慨:“就算陛下知了自己心中情感,仍然不愿在政事上放你一马。现在长珩回了边城,估计也用不了几日就会被调离,待我离京后,你身边亲信也不过尚且在驸马身边的文长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童怜笑道,“你本就有出色的才能见解,若非与我关系交好,当初怕也不会被他随便寻了个理由降职,长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