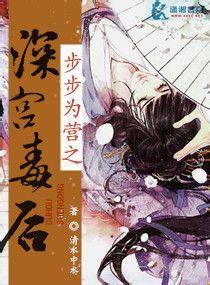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合约战争 > 第116章 忌日(第2页)
第116章 忌日(第2页)
“不行。”
宋西岭把杯中的吹吹起一圈圈涟漪,热乎乎的白气染上了他的眼镜。
“我必须得回去……就一天。”
傅珩之加重了语气。
“为什么?”
傅珩之沉默了。
“你不说的话,就不可以。”
宋西岭打了个呵欠。
“我母亲的忌日,”他低声说,“我每年都去。”
宋西岭举着杯子的手僵直,片刻后他说:“那,我和你一起去。”
这是他第一次和傅珩之一起坐飞机,踏上回国之程。
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傅珩之的家乡。
湿冷的空气顺着江南的毛毛雨化为水汽,从裤脚和袖口渗入皮肤,化为细密的针,见缝插针地扎入一切裸露的肌肤,他穿着一条单裤和一件衬衫,在十几度的天,竟瑟瑟发抖。
傅珩之拦下计程车。
逼仄的空间内回荡着不知名的音乐,间或溢出广播主持人无聊的对话,是他听不太懂的口音。傅珩之和司机交谈,也说着那种奇怪的语言。
末了,他低声问:“你在说什么?”
傅珩之也低声回答:“确认了一下目的地。”
到墓园门口的时候已是傍晚,雨已经停了。
傅珩之停下脚步,看着阴沉的天:“要不要进去?”
宋西岭犹豫。他其实不太想进去,他不认识傅珩之的家人,也没想过会认识——即使这是一位过世的人。但是一个人站在公墓门口,天色昏暗……
傅珩之忽然牵起他的手,慢慢地走进去。宋西岭没有拒绝。
偌大的公墓没有人,十分寂静,屹立着数不清的墓碑,宋西岭抓着傅珩之的手,越来越紧。
傅珩之忽然侧目,问:“没来过这种地方?”
“没。”
宋西岭老实说。
他连他爸的坟都没去过。小的时候,他妈不让去,后来长大了,一不知道地方,二也没什么想去的念头。即使他爸离世,后来的好几年里,他也怨恨着他。因为他,他们家才变得支离破碎,也是因为他,弟弟的病迟迟不见好,还产生了更多的心理问题。
傅珩之用力回握着他的手,温暖的体温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宋西岭的掌心,他感到心安了些。
他们在一座墓碑前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