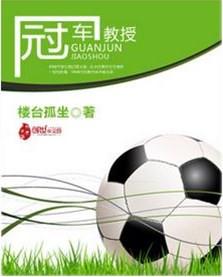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云水映花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众人议了半天皆建议围城。海目仓皇逃至闭城不出,城中并没有储备粮食。笼中困兽,料他也支撑不了多久。
元赫沉默不语,众人的意见倒是跟他不谋而合。只是围城又要多拖延时日,实在不是上策。
众将等他定夺。
“暂且如此吧。”元赫一锤定音。眼下着实没有什么良策。这一仗虽然胜券在握,却与他当初的速战速决背道而驰,想到这他不由得心中有些烦躁。
他疾步走出大帐,回头喊了一声:“商容,带一队人随我出去一趟。”身后的商容应声而去,片刻领了一队亲兵过来……赵凿也跟了来。
元赫一皱剑眉,飞身掠上惊风马,疾驰而去。身后商容急忙领人跃马跟上。
惊风马似是久未驰骋,放蹄狂奔。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似是阵前的嘶杀之声,空气中杂着草的清新与莫名的花香,本是踏青游春时节,而此时城外杳无人烟,百姓早早地就四处逃串,远离这兵戈相争之地。
元赫在一处高岗上掣马勒缰,极目远眺。风吹草劲,遍野茫茫。
他看着随风而舞的劲草,突然心中一动,剑眉舒展,微微一笑。身边的商容看着有些动容,多日不曾见他展颜,艳阳和风中,他战袍翻飞,星目熠熠,真是风神磊落。
元赫回头看着赵凿,说道:“你回去领着三千兵士去割草,另三千兵士扎草人。”
赵凿一愣,与商容对视一眼,而后有些恍然大悟,抱拳说道:“侯爷好计谋!”
元赫微微一笑,纵马回营,下令驻营休整。
翌日亥时,元赫下令攻城,铁甲兵推着战车,上立身着景国兵服的草人,夜色弥漫中,海目看不分明,以为景军趁夜攻城,仓皇中下令放箭。元赫只管令人在城下鸣鼓呐喊,并不近前。佯攻了半个时辰就鸣金收兵。回来后细细一看,草人上扎满了毒箭,元赫令人小心将箭收好,以待异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连着几日,景军都是夜里突袭,白日按兵不动。搅的海目夜夜惶恐,那毒箭也损失的十之八九。
元赫本想再有半月便可攻城,却没料到第十二日上,海目居然将城中老弱妇孺几百人带至城墙,命人推了下来。元赫在城下看的目呲欲裂,竟没想到海目如此丧失人性。看来城中粮草告急。
元赫紧抿双唇,吩咐李用召来手下诸将。片刻,诸将汇集中军大帐,神色肃穆。
元赫扫了一眼帐中的诸将,皆是他亲自挑选,其中不乏初涉战场之人。
出师之际,景帝元玠私下召见他,神色有些担忧,海目虽不足惧,但也不容小觑,元赫举荐的新人如何,着实也让元玠忐忑。元赫笑着说道:“皇上只管放心,哪个老人不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如今景汤十七年没有战事,却不可懈怠,正是培养些新人的时候,让他们去云南历练历练,权当是场练兵。”元玠微微颔首,将兵符极慎重地交付给他,说道:“景国就交与你和四弟了。”元赫接过兵符,小小的一个虎符卧在手心,触手冰凉,却又让人血热,元赫紧紧握住,顿觉沉重。他抬起头,元玠正定定地看着他,双眸一如当年坦荡如镜,虽然他登基已经四年,却仍然与以前一样,对自己不似君臣,却似兄弟。
帐中的几个年轻将领,商容机敏,赵凿勇猛,杨落沉稳,这一路下来,他们果然没有让元赫失望。
帐内静得只听见呼吸。
“看来海目粮草已经告罄,我本想再拖他几日,叫他自乱阵脚,却不想他如此凶残,将百姓视同草芥。攻城已是迫在眉睫,不能耽搁。”
元赫顿了顿,目光转向刘也:“你安排一些运粮车,外置干草,专从南门外经过。”
刘也有些不解,运粮车一向力求隐蔽,以防突袭,如此明目张胆必定是有原委。他没有多问,小侯爷虽然年轻,却是心智过人,此次领兵乃是皇帝力排众议,执意任命。这一路领兵下来,攻城掠地有勇有谋,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元赫又道:“南门的粮车由商容负责。”
刘也这才问道:“侯爷的意思是,有两队粮车么?”元赫点点头,说道:“你负责的粮车一切照旧,不可让人看出端倪。”
元赫又看看商容,赵凿:“海目龟缩于城内,若能诱他出城……”
赵凿顿时心中一热,急切地看着元赫。
元赫目光却扫过他,落在商容身上,微微一笑:“你不是一直有些抱屈跟着我坐镇,没有立功的机会么,眼下,这一仗成不成,可就靠你了。”
商容一听,顿时眼神雪亮,一抱拳头,恨恨地说道:“待我拿住海目老贼,为城中百姓报仇。”
元赫点点头:“明日起,便将南门的守军撤后掩在林中,骑兵在前,听你号令,步兵由杨落指挥。你挑选军中箭法极好的埋伏在南门外,随时待命。”
商容听罢,扑哧一笑:“军中箭法最好的就是侯爷您了。”
元赫嘴角微扬:“我倒是想一箭射死海目。”可惜他龟缩城中,死活不出。
元赫又道:“将火药埋于车上,外面覆盖粮草。明日起,一天两次固定时辰从南门送至东门。待海目出城抢夺,你们抵抗片刻就假意逃散。”
商容凝神细听他的部署。
“待海目抢了粮车从南门入城之时,即刻令弓箭手放火箭点燃粮车,炸开城门之后,商容领三千骑兵冲入城内,杨落的步兵随后入城。我与齐将军去攻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