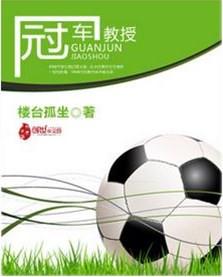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云水映花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林济舟将伤口包扎好,长出一口气转过身来,额头赫然汗珠莹莹。他对着元赫长鞠一躬:“多谢侯爷相救!”
元赫似梦中惊醒:“令爱的伤势?”
林济舟爱怜地看着女儿:“还好只是皮外伤,不过,我看溪儿吓的不轻。”林芷溪已经睁开眼睛,轻声说道:“爹,我那有如此胆小,我不碍事。”
“快谢谢侯爷!”林济舟轻推女儿的胳膊。
林芷溪鬼门关转一圈,正暗自庆幸,听了父亲的话才想起来眼前还有个大恩人。她忙感激地看向元赫,只见他怔怔地盯着自己,神情难测,心中有些不明所以,遂浅浅地笑道:“大恩不言谢,日后有需要小女子的地方定当倾力相报。”
林济舟道:“侯爷还有需要你倾力相助的时候么,真是小孩子家。”
元赫闻声收回目光,心头仍是起伏不定,但此刻形势紧迫不容多想。他快步走到门外,只见黑衣人已经死伤过半,尚有几个拼死抵抗,台阶上商容困住了欲冲进荣华厅的两人,元赫一剑架在其中一人的颈上,那人顿时长刀落地,青石上当啷一声。余下几个人很快束手就擒。
元赫冷眼看了看这几人:“我知你等是海目手下,只是如何潜入城中?”那几人倒是嘴硬,并不吭声。
元赫见他们哑然无声,沉默片刻没有追问。他侧身扬头,看着天际明月,暗声说道:“如此良夜,不知你等家人是否在祈月焚香以求平安。”他的声音低沉严厉,静夜之中如捻琵琶,带着蛊惑与威慑。林芷溪只觉心中一动。
说罢,元赫回头看往几个黑衣人,火光中他目光咄咄:“若是家中尚有父母妻儿,何不给自己留个活路。”
半晌,终有一人低声说道:“我等是副将里融手下,白日城破时,我们未来得及突围出城,换了衣服藏在一户民居。入夜后本想潜出城去,却见守城戒备森严,没有出路。里融说,既然是个死,索性死的轰烈些,若是能,能杀了景军主帅,也值得。”说到此,他怯怯地看了一眼元赫,却见他不动声色,又接着说道:“这府邸原本我们就住了许久,地形也熟,就趁夜来了。”
果然如此。元赫抬步迈上台阶:“商容,将他们与海目押在一起。”
商容领着几个俘虏而去,留下几个亲兵将死尸拖走。
林芷溪站在父亲身后,闻着血腥之气,顿时一阵反胃。她跟着父亲也处理过受伤之人,也曾帮邻居接生过,并非惧血之人,然而,战场上的血却是另一种味道,让人触目惊心。
林济舟正欲带着女儿回后园,身后传来一声:“林大夫,一会便会调人过来加强戒备,你只管放心歇息。”林济舟与林芷溪忙回身谢过,只见元赫站在荣华厅的门口,身影修长,长剑弩弓,周身如同罩着一圈淡光。
林济舟惊魂不定地回到后园,片刻工夫,果然见园中多了许多巡夜的士兵,这才放下心来。林芷溪摸摸脖子,笑着说道:“爹,没想到仗打完了,我却受了伤,看来云南之行定要给我留个印记呢。”
林济舟看着女儿的脖子又是一阵心疼,顺便就恼起林芷原来,恨恨地说道:“待我回了蓉城再与那小子算帐。”林芷溪忙打住不敢往下说了,转而问道:“侯爷叫爹过去,商议什么?”
“是问毒箭之事。依我看,应该是见血封喉,及蛇毒。”
林芷溪一听这两个名字顿时一阵鸡皮疙瘩。来太夜城几个月,她对这两样已不陌生。前者是当地罕有的毒药,本是猎户用于狩猎之用,没想到此次被海目用在守城之时。而蛇毒,也是极难治愈。二者掺和在一起,自是立杆见影地取人性命。林芷溪暗暗祈祷,但愿天下太平,永无纷争。
白玉有瑕
翌日清晨,林济舟便去荣华厅拜见元赫:“侯爷,经此一战,应有不少士兵受伤,在下愿献薄力以助军医施以救治。”林济舟生平最爱的便是治病救人,元赫又有救女之恩,自己一身医术怎好闲在府衙里吃闲饭?他自然尽心尽力地想要一展医术以做回报。
元赫一向爱惜手下,多一人多一力,林济舟又在此地停留了数月,想必对当地的毒物也多少知道一些,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如此甚好,林大夫是蓉城名医,只管放手去做。那毒箭的事也请多费心,若是能配出解药再好不过。”说完,他转身叫了一声李用:“你带林大夫去找孙将军。”
林芷溪一个人坐在厢房里看着一本苗人的医书,找来找去也没见到雪繁草的蛛丝马迹。顿时有些心思不定。她本来一心也想跟着林济舟去救治伤兵,虽说医术比不上父亲,好歹也能帮上忙。可惜父亲是死活不肯,嘱咐她千万不要出了府邸。战后初定,一切都要小心。林芷溪无奈,自打母亲过世,他便把自己看的比什么都要紧。以至哥哥常在被训斥地灰头土脸之后抱怨他是拣来的。
林芷溪叹了一口气,又长吸一口气,入鼻便是沁人心脾的花香,她索性放下书,将头伸出窗外,蝶舞翩跹绕着怒放鲜花,静中有动,动中有香。林芷溪以手托腮,醉在其中。一只彩蝶停在窗前一片杜鹃花之上,她轻轻伸出手指想去抚一抚它的翅膀,蝴蝶顿时惊飞而去,她随着飞蝶看去,无意中却见拱门处身影一闪,瞬间消失。
元赫在拱门处徘徊了几趟,透过花砖之间的缝隙,隐约可见她就在窗前,姿容烂漫。此刻前去贸然询问,如何开口?从何开口?他竟有些一筹莫展。而此时蓉城远在千里之外,想要打探她的底细,只有密信回京安排,京中各派都有眼线,他并不想惊动别人。略一思忖,他决定还是先侧面打听打听为上。不过心里的惊喜与忐忑却比大敌当前更让他激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