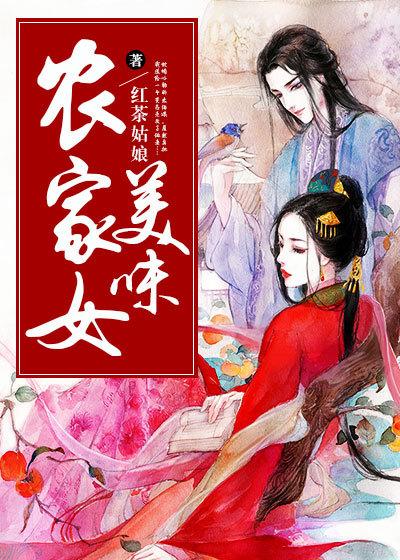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杀熟的经典语句 > 6 6(第2页)
6 6(第2页)
之所以买最新、最贵的游戏机,余奥是为了报复性地玩到昏天黑地。
结果,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家里也好,在和朋友们的聚会中也罢,他对游戏机避之唯恐不及。快乐的童年,错过就是错过了,补不回来。
工作之余,他也不大玩电脑和手机,偶尔来来回回地切换几个社交软件,明知不可能却还是要等一等“某人”的消息,谈不上费眼。
却有了两百度的近视。
他的金丝眼镜不是造型,摘下后,以姜半月和他拉开的距离,他只能对她模模糊糊看个大概。但无妨。她的讨价还价,他领略过太多太多次了。
他不用看,也知道她是怎样一副“嘴脸”。
十八年前的冬天。
姜半月将他从中学生的魔爪里救出来,离开时,还不忘回头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对他说再见,之后再见,却对他视而不见。
余奥不是个热烈的人,对好的、坏的,都不大在意——至少表现得不大在意。这是年少的他对抗余智梁的唯一一种方式,让余智梁好像一拳拳打在棉花上。于是,对于姜半月的翻脸不认人,余奥有不解、有不悦,也有不甘,但表现出来,也只是在上下学的路上,盯一盯她。
在一个九岁,另一个六岁的年纪,一个目不转睛,另一个刀枪不入,二人坚持了整整一年。
直到一年过去,又一个冬天,又一场初雪纷纷。
下午,姜半月和余奥各自坐在课堂里,各自望向了窗外。
曾经被虎背熊腰的中学生一边腋下挟一个的画面,都还记得。
姜半月托腮,想起那个中学生口出狂言,左一个老子,右一个老子,还说要为民除害。那天她还没学过除法,想当然地说你自己除自己,等于零。
前两天她学了除法,知道了自己除自己,等于一……
与此同时,余奥也想起了那个中学生。
那天他回家后,藏了狼藉的大衣,对余智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几天后,保姆把他的大衣翻了出来,交给余智梁。不等放学,余智梁让司机把他接回了家中。
余智梁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言不发。
不为别的,他就是想和余智梁对着干。
余智梁没打他,没骂他,也没让他饿肚子,而是让保姆带他去剪头发。保姆问剪多少。余智梁说剃光。
这下,余奥不干了。
他不怕挨打,不怕挨骂,也不怕饿肚子,但他怕丑。他不想以后在上下学的路上,让姜半月看到奔驰里坐着一颗鸭蛋。她不看他,不代表她看不到他。
就这样,余奥对余智梁投降了。
这是余智梁的“高明之处”。这几天,他看到余奥上学前总会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回家后,还检查发型有没有乱。
身为律师的他,对年少的儿子打蛇打七寸,易如反掌。
余奥和盘托出:“是你女朋友的弟弟。”
那天之后,余智梁将压力给到十八岁的小女友,道貌岸然地说他这个年龄,爱会屈从于现实,如果现实是她的家人不接受他,如果他的事业、形象和社会地位会被她“不懂事”的弟弟破坏,他只能牺牲他对她的爱。
如此一来,小女友又将压力给到了弟弟。
姐弟二人闹了个你死我活。
没多久,余智梁对小女友提出了分手。
他说他是为她好,不希望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做抉择。
最后,小女友肝肠寸断,弟弟离家出走,父母以泪洗面,一家人你怪我,我怪你,愣是没人识破余智梁玩腻了的真面目,没人怪余智梁这个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