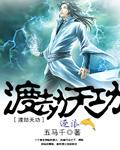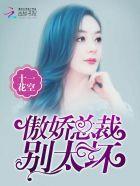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嘉靖帝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张璁听此,大为触动。恰巧,他在南京街头闲逛时,结识了一位擅长星相术的御史肖鸣凤,此人将张璁的面相认真观察一番,又推算了一阵,劝他千万不可停考,要再拼搏几年,因为从他的命相看是&ldo;从此三载成进士,又过三载当骤贵。&rdo;张璁想想王瓒的话,又听星相家这么一说,不觉心动兴起,便想既然已经考了这么多年,再试一科倒也无妨。于是,他又潜心读书,搏斗考场。正德十六年的辛巳科,时年四十七岁的他,果然中得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
当朱厚熜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内阁大臣,因兴献王尊号展开激烈争论时,正任礼部观政的张璁却在一旁,静观着这场君臣礼仪之争。他始终想着王瓒的话。凭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他深知&ldo;胳膊扭不过大腿&rdo;的道理。那一班老臣现在与皇帝争来争去,只因新帝根基未稳,自己又人多势众,暂时占得上风。但时间长了,谁胜谁输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对呀,皇上孤身作战,现在正需要有人站出来帮助哩。我如果挺身而出,助皇上一臂之力,说不定会应了王瓒和星相家的话,受到皇帝的赏识,重用提拔,一步登天哩。想到这里,张璁深深感到这是一次出人头地的绝好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
实际上,评议大礼是张璁政治学术上的强项。早在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正月,他在家乡创办罗峰书院时,就精通三《礼》,对此有过深入透彻的研究,还撰写出《礼记章句》一书。他抓住这次政治机遇,发挥议礼的学术优势,于正德十六年七月三日向嘉靖皇帝呈上《大礼疏》,提出与皇帝的观点相一致的主张。疏中有云:
真正的孝子,最重要的是尊敬双亲。尊敬双亲最重要的是要天下都照行。陛下嗣登皇帝位,即议追尊圣父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这是最大的孝道啊。
皇帝看到这里,禁不住点头称是,其孝道观点正与自己如出一辙。接着又看下去,只见疏曰:
廷议结果拿汉定陶、宋濮王的故事,说继承了皇位就应该为人之子,不得再顾私亲。天下哪有无父母的国君呀?汉哀帝、宋英宗虽固定陶、濮王子,然而成帝、仁宗都是先立为嗣,养在宫中,其为人后之意是明摆着的。所以说师丹、司马光的言论在当时是可以的。现今武宗无子,大臣遵照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为皇帝。遗诏直曰&lso;兴献王长子&rso;,并没有要您成为人后之子啊。则陛下登基,实际上是继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看到这里,小皇帝抬手啪的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侍立在旁边的德兴吓了一跳,慌忙跑过来说:&ldo;万岁爷,怎么啦?&rdo;
朱厚熜一听,反而不知所云,又反问道:&ldo;什么怎么啦?&rdo;他睁着一双专注的眼睛看着德兴,顿了一会儿又说:&ldo;哎,德兴,给朕拿点好吃的。&rdo;小皇帝索性站了起来,伸个懒腰,又蹦跳了几下才走到龙案旁。德兴已将一盘鲜荔枝放到他的面前,并剥好喂到他嘴里,小皇帝边吃边继续看下去。
大礼规定&ldo;长子不得为人后&rdo;,圣父只生下陛下一人,为了天下而为人后,恐怕自此将断绝父母之义。所以说在陛下尚未入继祖业就废弃尊亲是可以的,而入了继统再说为人后,以自绝父母亲则是不可以的。再说统与嗣是根本不同的,嗣是非得父死后,儿子才能立呀。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帝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如果必须剥夺父子之亲,另建父子之号,然后才叫继统,那么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都不能称为继统了吗?臣以为今日之礼,应另外立圣父宗庙于京师,公开张显尊亲之孝,旦旦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父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啊!
&ldo;好,好!此论一出,朕父子得恩义两全了。&rdo;小皇帝阅完张璁的上疏,忍不住称赞,无比畅快,得意忘形,你道这是为什么?
------------
章七跳出漩涡逆流而上(3)
------------
自从皇上登基,提出父母的尊称以来,已愈几月,尊称未定,却与杨廷和为首的一帮大臣斗得筋疲力尽,闹得朝廷风烟四起。看了张璁的奏疏,小皇帝心里终于豁然开朗,眼前的大道宽阔无边。显然,疏文不但给小皇帝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将杨廷和引为法宝的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与自己的继统严格区别开来,把这两件性质根本不同的继位之事再往一起扯就显得有点可笑了。小皇帝好像自己已经掌握了天下最锐利的武器,天不怕地不怕了,于是立即派礼监官员将疏文送至内阁,并宣谕阁臣道:&ldo;这一理论才是真正遵循了祖训,又根据古礼,你们不要再误朕了!&rdo;
杨廷和仔细看完张璁的上疏,很不以为然地将它丢至一边,漫不经心地道:&ldo;哼,新进书生懂得什么国体!&rdo;又立即把张璁的疏文封好退回。
是啊,谁又能理解杨首辅的一片苦心呢?自从小皇帝登基以来,朝中所有大小事宜,皇帝都要请教他这个首辅,在他眼里,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顽劣不化的孩童。唯有在对待父母尊称这件事上,他似乎想自作主张,不请教我首辅,就想凌驾于我等人臣之上,将事情顺顺当当办成。哼,我叫你办成?没那么容易。杨廷和牢牢记住张皇太后的话,不能让他随心所欲,当遏制的就要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