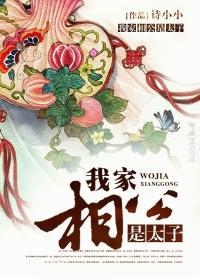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地府是否存在 > 第112页(第1页)
第112页(第1页)
祝海月看着不愚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斜了一眼白镜,“不愚好歹事出有因,他有情有义,不过是怕你吃亏。我倒觉着他没什么错!”得了这句话,不愚偷偷破涕为笑,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祝海月:“不过歉还是要道的,你自己看看刑大叔的脸都成什么了!你师父说的没错,他要是不顾你的安危,你连近他身的机会都没有。”“知道了娘娘,我再不敢了。”“下去吧。”不愚看看他们俩,“那我现在就找刑大叔赔礼去。”祝海月:“别别,刑大叔和师师姑娘还有事要说,你晚点再去。”不愚“哦”了一声,抬头看向白镜,“师父,那我们也走吧。”祝海月:“不用,我也有事要和你师父说,你自己先下去。”不愚走后,剩下二人都等着对方先开口,最后还是祝海月等不及,先打破沉默。“师师积怨已久,有些事说出来未必不是好事,你何必跟她置气。”“……”白镜一怔,“你都知道?”祝海月无奈地笑笑,“我是不拘小节,心思也不如师师细腻,可我也不是木头,谁对我有什么心思我还是能察觉到的,更何况是容琏那样的人,以他那样的身份,许多事情他本没有必要对我那么好。”说完,她一挑眉,“我知道不稀奇,可你是怎么知道的?”“阿清告诉我的。”祝海月不信,目光炯炯,盯着他。“你有很多事情还瞒着我。”她直接给他定了罪,她算是彻底明白了,很多她没有说的事情他竟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弄了个了如指掌。“每个人都会有秘密,你也并非事事都告诉我。”他垂眸。“想知道什么你问我啊!”“……”祝海月:“我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可你不该去偷看我的过去!”她很笃定,能那么了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偷偷看了她的生前。“我没有看你的!”白镜第一时间否认,虽然有些难以启齿,却已经不得不说,“我看了师师的……”“师师的?”祝海月更惊住了,“你看她……”一些香艳的想象浮上她脑海。“……不该看的我没看!”他很尴尬,“她自己的事我不想知道,我只是循着与你有关的踪迹探查了一遍,我总要确保她对你无害。”他一直对师师抱有敌意,如此说来倒也算有理有据,祝海月接受了这个解释。“我一直觉得当初殿下只是混淆了我们之间的情义,毕竟我们几乎是同时长大的,彼此既是主仆,也是兄妹。我对他和王爷忠心耿耿,想必是他将这些情感当做是男女之情了。”白镜听了心中哑然,他还当她从来都不懂,原来竟是他多此一举,特意问她:“既然同是一起长大,你倒又分清你与阿清之间就是男女之情了?”祝海月白了他一眼,懒得在事实上与他争辩,只继续说道:“当初我以为他用不了多久就能明白这些情感的不同,区分得出我与他只是主仆再无其他,可是……”她摇了摇头。当年寿州之战,她没有按圣上的意思和平退守,而是以一招弃车保帅,换得宣朝惨胜。大捷归来她进宫上交虎符,晚宴上却滴水未进,散席后,彼时身为太子的容琏亲自劝慰她。那一战,损失精兵两万余人,刑干是那两万人的将领,他就是在那一战中命丧黄泉的。容琏说朝中虽有少许奏折参她,但他与父皇都深知她的不易,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保家卫国,她没有错。那晚他们一起喝了许多酒,她心中痛苦,越喝头脑却越清醒。容琏酒到浓时兴致大好,非要给她讲故事听:“我近来,听了个故事,说给你听!”“传闻,张献忠有个美娈童,年十八,技武绝伦。其与靖南侯黄得功对阵时,一箭便射中了黄得功的手。黄吃了败仗,勃然大怒,伏兵将少年生擒。见面后,黄亦被少年的美貌与英勇所倾倒,想收为己用,奈何少年誓死不从,黄百思不得其解,笑曰:‘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故事讲到这,容琏看她的目光已是炙热,她却仰头灌下一口御酒,以此搪塞。容琏笑意朦胧,好似有心挑破,特意问她道:“换作你,你降否?”祝海月答道:“殿下,海月是您和陛下收容养大的,我生是宣朝的人,死是宣朝的鬼,绝无降于他人的那一日。”那时她甚至拿不准容琏究竟要试探的是她的忠心还是其他。见他看着自己不说话,祝海月问道:“后来呢?那少年降了么?”容琏摇了摇头,“少年与你一样,坚决不降,最终绝食而亡。”他起身,绕到祝海月这边,与她一同坐下,此举仿佛一块滚烫的炭火掉到了身边,令她正襟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