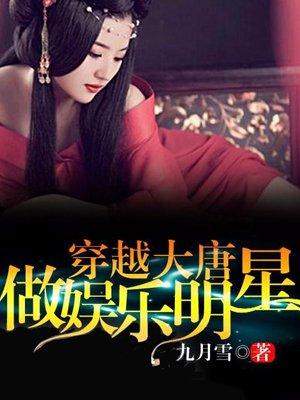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与妻书佟大为朗读 > 第124章(第1页)
第124章(第1页)
他看到了若莲。真奇怪,他就这样认出了她。那明明只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年妇女的轮廓,可他就是知道那是她。平静地知道‐‐并无什么汹涌激烈的情绪,并无什么忐忑不安的疑真疑幻,甚至并无迅猛而至的,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他平静地朝她走去,并且他也知道若莲此刻心中所感与他一模一样。
一直要到走出十几步以后,他才开始觉出一点激动。这点激动和过往数十年间的任何一种激动都不同。它是甜的,又是酸的,还是苦的,更是一种满‐‐充盈于胸腔之中,满满地塞着,热辣辣的一团。他的脚步加快了一些,远处的那个轮廓再清晰了一些,胸膛里的那点激动慢慢沉下去,变成了静水流深的那个深。
到得李子明终于站在若莲面前的时候,他们俩相视微笑。他在她轮椅旁的草地上席地坐下,和她一起看向绿森森的葡萄园。过不了多久,叶子会转黄,葡萄会一日一日地大起来,甜起来。
&ldo;今天天气真好。&rdo;他说。
&ldo;嗯。这里大多数时候天气都很不错。&rdo;她说。
那一天,他们在这片树荫下晒了好久的太阳。其间刘勇在他们的家里招待了李子明的家人,将午餐和若莲的药用野餐篮一起送了过来。还送来了一张白色的藤椅。
那天有很温柔很温柔的风,他们说的话全都飘散在了风里。那些话语和笑声长出了蝴蝶的羽翼,飞去所有错过的别后光阴,将所有皱褶一一抚平。
&ldo;这就是告别了。&rdo;若莲想,&ldo;这样的告别真的很好。&rdo;她对李子明伸出手去:&ldo;约个来生。&rdo;李子明将手伸过去,喉头轻轻一哽,&ldo;约个来生。&rdo;
第99章
和李子明的重逢是若莲生命尽头预支到的甜头‐‐最后之战是在肿瘤全面扩散之后打响的。癌细胞扩散到她的气管,每一次呼吸都似乎要耗尽全部力气。剧烈的疼痛如附骨之蛆,死死纠缠。到此时此刻,包括小凤仙和刘勇在内的全部家人已经都无能为力,宁平和宁秀赶了过来,他们要做的,是尽量减少若莲的痛苦,企图挽救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尊严。但是医学能够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小,止痛药的使用效果越来越差,不过是将绵绵不绝的疼痛转化为浪潮一般的疼痛,为若莲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除了痛,还有整夜整夜不能入眠,无法躺平,永远呈九十度靠在床头。昏迷是奢侈的,虽然就算昏迷了也在痛。
若莲对周遭的一切感受得到,但是已经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她觉得自己似乎被绑上一条注定要沉没的破船,风雨肆虐,颠簸、痛苦无休无止,无力反抗。这样的感觉常常和南京经历错乱,她甚至觉得现在就是在南京,不同的是,这一次,身边没有刘勇,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在这种时候,那些被理性死死压抑一生的恶念一次次袭来,她狂怒地抱怨命运的不公,刻薄地觉得刘勇是个无法沟通的农民,甚至明目张胆地嫉妒李子明的太太,甚而至于,觉得李子明也无非贪图情事之欢。这些恶念席卷着,汹涌着,又冷又黑,势力强大,一波一波要将她淹至没顶。然而,这所有的斗争都只在她的世界进行。身边人只看到一张隐忍的,痛苦的,无力的脸。
此刻,如果有信仰是否会好一点?如果能够相信真的有彼岸是否会好一点?上帝或者别的神是可以永远在一起的,当孤军奋战的时候,当快要被恶念吞噬的时候,当觉得人世间的所有阳光都照不透黑暗心房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偶尔清醒的时候,若莲在心里问自己。她真心希望有谁能够在她旁边念个金刚经或者唱唱赞美诗什么的。也许还是不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
最后的一个月,若莲唯一能有的坚持就是自己起来上厕所,尽管还是需要人在便后帮忙清理,但她坚决不肯在床上解决,就算是用便壶也不可以。尽管每一次挣扎下床都又痛又疲倦,坐回去以后还要喘上半天,竭尽全力才能吸得新鲜空气,在窒息的边缘来来去去,可是,她还是坚持,她把有限的体力全用在这件事上了。所幸宁秀完全明白她,温柔又熟练地扶着她的手,带她一步一步挪到洗手间。小凤仙也是这样,虽然她的手法不如宁秀,偶尔会令若莲觉得多痛了一点,但还是令她觉得安慰又感激‐‐是的,有时候,那个理智的正常的若莲会回来,善意和温暖会闪回。可,还是恶念占着上风,这其中最不可遏制的是:我一生没有怨过谁,我一生不曾快意过。似乎要将所有的克制隐忍所有的委曲求全全都补偿回来。
终于,她开始发脾气。恶念终于如决堤洪水,开始外泄。不是控制不了,是不想再控制。家人全都理解她,给她更多的安慰和关心,但是没有用。她开始折腾‐‐因为自己无法入眠,要求刘勇和小凤仙一直醒着陪伴,要听他们读书,要说话,要半夜起来听音乐。白天黑夜,无休无止,不许轮班,如是种种。家人唯有付出更大的耐心,但体力终究无法支撑,大家其实都不再年轻力壮。疲惫加上焦虑,一日一日,神色憔悴,人人都是气力用尽的模样。当若莲的善念偶尔闪回的时候,她痛恨这样的自己,这种痛恨又加剧了下一轮发作的烈度。同时,她开始疑神疑鬼,觉得就算是至亲家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这一刻觉得不能接受是应当的,下一刻又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印证,期待他们会接受。等他们接受了,她又觉得他们很可能是装的,说不定在心里期待她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