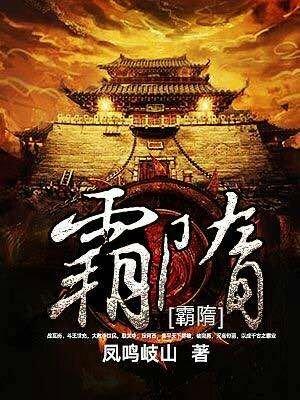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皈依者狂热by江JJ免费笔趣 > 第173页(第1页)
第173页(第1页)
由于一直在走路,血液始终没有凝固,倒是免去了脱下袜子撕扯皮肉的痛感。
何灿用水冲了一遍,接着拿酒精棉擦干净皮开肉绽的前脚掌,用纱布包好。两只脚他都独自处理完了,面不改色,连纱布都强迫症般打着很标准和对称的结。
他的脚比露在外面的皮肤还要白,脚趾也瘦削,指甲平滑整洁。只是此刻趾缝淌着没擦干净的血水,脚后跟也是,让他像刚刚上岸的人鱼,辛苦地在烈阳下晾着苍白的双足。
然后他认真收好剩下的酒精棉和纱布,重新放回兜里,转头和不远处站着的宗政慈对上视线。
“对不起,弟弟。”何灿笑了笑,抬手晃了晃用剩的那瓶矿泉水:“我知道你们搬水很辛苦,如果要分配的话,这一份就从我应该有的份额里扣吧。”
他拿走了两瓶矿泉水,洗干净两只鲜血淋漓的脚掌,因为很节约,甚至还剩下了一瓶。
矿泉水瓶在阳光下折射出并不刺目的光弧,像是何灿浅色调的虹膜,他的笑容比水还干净,堵死了宗政慈的兴师问罪。
大家都不怀疑何灿是想偷懒。
宗政慈怀疑。
大家都没在意何灿先拿走了两瓶水。
宗政慈在意。
甚至昨天围着篝火而坐的晚上,何灿透露了自己困难的家境,后来因为夜深后他和蓝靖童亲昵的表现,宗政慈开始认为所谓的“贫穷”不过也是一种话术,是某人示弱的手段。
现在正视何灿的脸,宗政慈才发现,原来惯说谎言的骗子也会说真话,一些习惯伤口才能练就的忍耐做不得假。
宗政慈少有的感受到无语凝噎,绝大部分时候他的沉默只是惰于开腔,没有什么想要出口表达的欲望。实际上因为他个人的存在感天然已经十分鲜明,所以也不需要靠发声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某种程度来看何灿是他的反义词,虽然本身同样足够优秀,却还是不停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他人目光,证明自己存在。
许久之后,宗政慈才说:“痛吗?”
何灿非常意外地看着他,说:“当然痛。”
宗政慈回应:“痛就对了。”
何灿:“……”
果然宗政慈还是那个宗政慈,何灿被他梗住,一时都没想好作出什么表情。却见对方迈开长腿朝自己走来,俯身握住了地上的矿泉水。
这回何灿是真的震惊了,不会吧,连一瓶水都不留给他?
然而,下一刻,宗政慈另一只手拎起了他的靴子,接着用胳膊抄住他的后背和腿弯,将他打横抱了起来。
何灿下意识搂住他的脖颈。
由于宗政慈双手都拿着东西,所以手掌并没有贴在他身上,而是仅仅靠着小臂内侧承托他的重量。以往宗政慈总是穿着卫衣,正式开始求生了才换成迷彩外套。此刻他的外套绑在腰间,上身只一件黑色紧身背心,入目所及处胸膛两肩的轮廓肌肉非常明显,让人意外于刚刚成年的男性能拥有这样一具富有力量感的身躯。
看不见的地方,何灿能感受到他小臂绷紧的肌肉硌着自己的脊背,少了手掌接触的发力方式比正常横抱困难许多,却多显出了几分克制和不冒犯。
不过,何灿没有这种距离感。
回过神来后,他放松身体靠在宗政慈身上,甚至抬手用手指去碾动对方的耳垂。
慢吞吞地问:“弟弟,你干什么?喜欢我了啊?”
宗政慈面色不变,偏头避开他的动作,冷静道:“我同情你。”
又是这句话,产生的伤害却已经大大降低。何灿笑起来,很无所谓地说:“还有些人一开始很恨我呢,最后也会喜欢上我的。”
话音落下,宗政慈的脚步顿住。
何灿侧眼,看见几步外站着的蓝靖童。
宗政慈忽然俯首,嘴唇几乎贴在他脸颊上,压着嗓音问:“你说,你刚刚说的话,他听到了吗?”
何灿却完全没有放轻声音的意思,很坦荡地对着不远处的蓝靖童笑了笑:“弟弟,我都不担心,你为什么要压低声音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