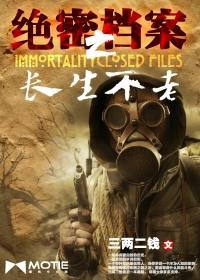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我捡的鲛人怎么会咬人作者鳈客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我娘因为那个秘密,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受孕,可她见那个怀孕的女人如此受宠,以为自己是因为没有孩子,才失了宠爱,于是拼着一搏,生下了我。”
商别云好像彻底睡着了。魏澜轻轻扯开自己的衣襟,两肋之下,有两排形状奇怪的肋腮,一半闭合,一半歪扭地开着。
“没想到,果然生出来一个怪物。”魏澜又笑了:“这下我爹吓坏了。他不敢将我娘与我赶出门,怕败坏了家族的名声。便将我们拴在柴房里,像狗一样养着。我娘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争气,长成了怪物,这才害了她。我在柴房每天挨着她的咒骂跟踢打长大,长到十二岁,我爹突然发现,我好想继承了我娘的脸。我没见过他几面,第一次见面,他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出来,只要听他的话,他会给我好吃的。”
“能离开那个疯子一样的娘,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顾我娘的咒骂,疯狂点头,他将我带了出来,把我洗干净,用布条缠住了我的上身,告诉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别人看到我肋间的鬼东西。他找人教了我几年,让我认了字,懂了些礼仪。”
“后来有一天,爹带来一个客人,叫我去陪着。我高兴坏了,爹从没让我见过人。我去了客房,爹却不在,只有那个客人……”
魏澜的声音在这里停住,没有再说下去。
商别云突然醒了,咕哝着,要水喝。
魏澜倒了杯水,递在了商别云唇边,看着商别云喝水,他突然笑着问:“别云,你有没有想过在岸上,在这里,长久地生活下去?”
商别云喝了水,稍微醒了醒酒,闻言不假思索:“不会,我只是贪玩个几年,正事却是不敢忘的。”
魏澜眼神里的光明明灭灭:“哦对,你说过,你背负着你们族中王的血脉来着。”
商别云烦躁地挠了挠头:“真烦,你不知道,海里什么都没有,没意思极了,我要是普通人就好了,就不用管这些东西,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魏澜突然将手肘撑到桌子上,笑着开玩笑道:“既然这样,那不如你在这边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彻底定居下来吧。这样我还能时不时地找你喝喝酒。”
商别云却突然大笑起来:“哈哈,说什么呢你,我跟人族的女孩怎么在一起。就好比你是人,难道你会跟螃蟹结亲?生个什么出来?生个小螃蟹人?”
魏澜突然愣住了,半晌笑了笑,低头喝了一口酒:“嗯,也是。”
商别云觉得他脸色有些不对,伸手想去摸摸他的脸:“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烧?”
魏澜躲开了他的手:“没事,过会儿就好了。”他又递给商别云一盏酒,笑着说:“来,喝你的酒。”
商别云接过他手中的酒杯,一仰头吞了下去。
作者有话要说: 不好意思今天聚餐晚了一些,四千字长章奉上。
第60章
商别云躺在地上,呆愣愣地,望着头顶铁幕一般的天穹。
那天穹此时却斑驳了下来,一块块黑色的天幕坠落下来,在远处发出坠地的轰响,头顶的那块天幕也摇摇欲坠,将要陷落。
商别云一动不动,不想躲,也不必躲。
那片天幕带着最后一偏记忆的雪片,直坠下来,携着万钧的威势,将商别云的整个身体,压在了下面。
痛。
无法言喻的痛从头颅身体四肢乃至整个躯壳中传来,那像是要从身体内部将人活生生撕成两片的痛,将商别云的意识从无垠的空虚中唤醒。
可是他却发现,意识与躯壳好像已经被撕成两片了。他被困在了自己的躯壳里,无法挪动一根手指,也无法掀开一寸眼皮,连接在意识与身体之间的,似乎只有那令人发狂的、绵绵不休的痛觉。
他的意识徒劳地挣扎着、怒骂着,可却是徒劳。身体上又传来新的一波剧痛,他的意识渐渐失去了抵抗的力气,虚弱地瑟缩在痛觉的间隙中。
“别云。”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别云。”又是一声,声音那样的熟悉。
谁在叫我的名字?谁知道我的名字?谁在我身边?
魏澜。是了,想起来了,我在跟魏澜喝酒,醉晕过去了。发生什么事了?在我的身体上正发生着什么事?魏澜呢?魏澜现在怎么样?
意识抓住了那道声音,从痛苦的海洋中,浮了上来。
客房的床上,商别云睁开了眼睛。空气中弥漫着极其浓重的血腥味,他的身体还不能动弹,眼神四下一扫,与趴在床边,恰好抬起头来的魏澜对视了。
魏澜的嘴上、下巴上、脸上、前襟上,都沾满了鲜血。他的脸色透着不正常的潮红,猝不及防间与商别云四目相对,先是一愣,复又笑了,一边笑,眼泪一边坠下来。
“你怎么回事啊?”他自顾自地哭着,语气中有些埋怨,举起手来,给商别云看自己拿着的东西。
右手握着一把沾满了血的刀,左手上提着的,是一截血淋淋的、长长的断尾。
“你怎么回事啊!”他用手胡乱抹着脸上的眼泪,可只是将脸上的血抹地更乱了。他像是一个赌着气的小孩子,一遍遍地抱怨着:“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没告诉过我,它会长回来?为什么没告诉过我,它们都会长回来!”
商别云躺在床上,静静地流着血。除了身下,他身侧的衣襟也被利器割开了。暴露在空气中的肋腮上,血肉模糊,布满了刺伤、割伤、割皮、烫伤,甚至咬伤。饶是这样,各处伤口也几乎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