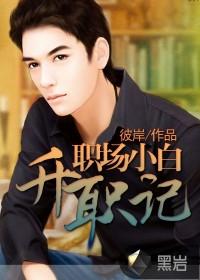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战锤40k碎裂钢魂免费阅读 > 帝皇的子嗣刀锋盛宴(第1页)
帝皇的子嗣刀锋盛宴(第1页)
库珀知道自己不是当忆录使的料子——即使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们家随身携带的摄像机仆都文采斐然,兢兢业业地替人类帝皇完成着记叙大远征故事的光荣任务,看起来他家的文字基因理应不差。
但说真的,他看见羽毛笔就头晕,一闻到墨水味就舌头苦。
也许某种意义上,他这才是涅克洛蒙达人该有的正常状态。字不一定要认识,但架一定得会打。
从白蚁窝一样支棱进天上的顶巣,到无数公里之下底部几乎要扎根进星球深处的散热管道边缘,所有小孩最好都得学着加入对应层级的帮派——除非家里突然撞了大运,那时候就能加入更高居住层的帮派。
然后,你纹了帮派的标记,多几个誓言,上供一笔金钱或者去搞几个人头来,你就能在这第二家庭的羞辱和庇护下,度过一段寝食可安的消停日子。也许五年,也许五十年,直到你死了,或者帮派覆灭。
如果情况是后者,你最好再找到一个本层级的全新大家庭,并祈祷他们的入会仪式不会消耗你身上过多的零件。
在涅克洛蒙达,几千年里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就算从上层跌落下去几个贵族,也最好别痴心妄想能有办法向上爬——你想,事情是这么一回事,上面少了一個姓氏,不是刚刚好能给某个缺少姓氏的私生子腾位置吗?
这人事工作的循环是人类走过黑暗年代的智慧结晶,除非有外来的光照把这个黑暗的蛋壳照亮,祖宗的铁律可不太能更改。
“没有外来的光照,”库珀的父亲说,边嘟囔边研究他咖啡里的拉花,思考着要不要督促家里的机仆去咖啡协会考个顶级咖啡师证书,“涅克洛蒙达没有外来的光照,只有外来的拳头——砰,第七军团,帝国的铁拳,一巴掌就把我们的天顶砸出个窟窿。”
“这是件好事,”他母亲抱着数据板飘过去,探出窗户,俯瞰顶巢的无限风光。混乱的钢铁在下方如同一层厚厚的污垢,堆积在灰烬荒原上,塞满了涅克洛蒙达的居住区。
“对我们家是好事,帝皇的差事把我们从中层提升到了王巢里头。”父亲终于喝了他的咖啡,“为了让泰拉来的船更方便把我们接走。”
涅克洛蒙达唯一的太空港就悬挂在他们头顶上,“月神之眼”空间站,只有它能够容纳轨道上的运输船。
一切运输和贸易都与它紧密相关,至于涅克洛蒙达是先有如今整颗星球最繁华的王巢,再有顶上的月神之眼,还是两者反过来——谁都说不清。
它们就有这么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巢都星球上中下巢的分级一样亘古不变。
“我不是在聊这个,”母亲翻了个白眼,捋了捋机械改造后还剩下的半头金,“我是说,自从人类帝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官方的擢升途径后,下巢打算通过胡闹一通上来的人一下子就少了。”
“你说得对,虽然行星防卫军和帝国之拳每年征招的人屈指可数。”父亲故作优雅地点了点头。
库珀不想听这个,说不准为什么,他不喜欢父母谈论涅克洛蒙达上下巢关系时的腔调,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父母总是有道理,他不确定地想,也许——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听他们这么讲话,承袭他们的意志。
但不是今天。
他跳下餐桌边的高脚凳,打算出门打架来释放他莫名不太舒爽的心情。
他不是能和其他小混球们搞起来的儿童帮派混得来的人。他就是不想陪他们吸欢乐水,还有不觉得欺负下层的小流氓有多大乐趣。
不,他就要按自己的心意,和同他在地位上势均力敌的人狠狠来一架,不论对面是谁,有多少把短管枪。
他就是无所畏惧,喜欢战斗,热爱单枪匹马地把对方身上那一袭香喷喷的丝绸袍子扯下来,顺着风扔到下巢里头去。某种意义上,他觉得这是他的荣耀——尽管他还摸不准荣耀到底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库珀是个独行侠。
出了门之后,库珀现外头今天空得惊人,大街上没有乘着飞行滑板四处乱窜的混球,也没有一骑绝尘的双轮车队。
他想了想,眯着眼睛抬起头。果不其然,天空上飘着一圈悬浮的飞行器,一堆亮堂堂的明黄色小点。帝国之拳从太空中班师回朝,派出一支舰队回了他们的一大征兵地。
自从第七军团把涅克洛蒙达从兽人的威胁里拯救出来后,伟大的人类帝皇就特批允许他们在此征兵。
每当他们的远征舰队悬在空中,整个涅克洛蒙达——能够看见他们的那一部分,缩在中下层不见天日的居民不算——都倾巢而出,跑去围在帝国之拳的堡垒外头,祈祷着自己能在任何层面上时来运转。
库珀搭上轨道车,好奇心让他也决心去一探究竟。他在外围兜了几个圈子,无法突破眼前的人群,而他的身高也不足以让他看清这出乎意料的拥堵到底源自何方。
他随波逐流,跟着人潮前进,渐渐混进一群和他同龄的男孩队伍里,并靠着纹身辨别出那个和他有点旧仇的中流崽子小帮派。
他上次撞上他们抓着从下层带上来的男孩,要从塔尖上推下去,以便测一测涅克洛蒙达地心引力的常量。他们过度的得意洋洋给库珀提供过一个完美的突袭契机。
他没看见那些顶级大家族的上流公子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在。
那帮混球明显看见了他,库珀等着他们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