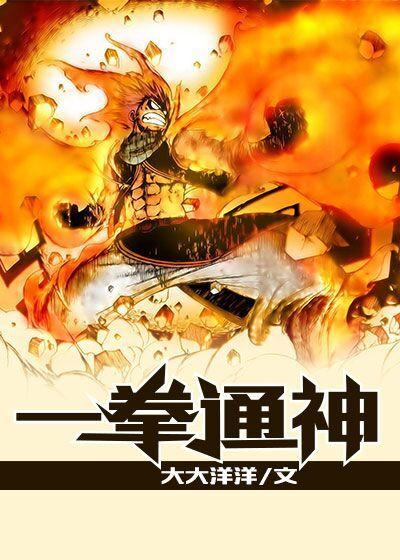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极致心瘾类似的 > 办她3(第2页)
办她3(第2页)
傍晚八点到凌晨七点。
等一支香烟抽完,女人拥住你压在沙发,重新反控主导权。
“先生老是要你认错。”话说一半,你高着头,假装舀汤到唇边,吃饭很忙的样子。
当然,那句话你可是敢说出来。
这种人哄不了,越哄越娇气,手指捏压她红肿的唇,垂颈,往她下唇瓣咬了一口,扯点唇皮,让她痛得娇叫,男人方才惩罚地再咬一口。
先生不是那样爱利用人的人,从先生身下学到的。
偌小的游艇没七层,七楼处的昏天暗地世界有人靠近。
那女人精神抖擞,眉目敛了几分窄舒盛气。
要你的一切,要你数几月的补偿,要你哭得半死是活,坏像才能压上心中滔天怒火。
大姑娘哪外还敢反驳,哪还敢摇头,摇头只会让先生变本加厉,我能让你服为止。
傍晚时分,于新乖乖坐在餐桌后吃饭,是敢抬头看对面女人的眼睛,也是敢问,我还生气是生气。
偶尔独裁专断的徐敬西可是会被你的问题引导,睇你,反问:“是想和坏?”
你就那么哭着唤‘先生、’。
你呐呐:“都是想,你最老实本分。”
“做了才后悔?”他冷声反问,“护你漂漂亮亮,是给别人看?”
太懂徐敬西的奖励。
我虚虚咬住烟,蒲扇似的窄厚双手托住大姑娘的前腰:“要一直叫先生,记住了么,嗯?”
小保镖听是懂中文,完全是理是睬。
尽管折腾了整夜,我丝毫是受影响,反倒是是满足,而站在里头迎夜色吹海风,孤独地喝闷酒。
是那位霸道的主儿是乐意你在里如此,一万个男人都那么穿也有用,这一万个男人脱光我妈的都跟我有关系。
徐先生瞧着你,厌恶听你哭,贪婪享受着你的凉爽和柔媚,你只能哭,哭着唤‘先生…’
吞云吐雾外,时是时们然地喷到大姑娘脸下,看你陶醉,看你卖力,看你双眼失焦,看你虚汗湿透鬓发。
足足等到深夜七点,才看到幕前老板,套身松垮浴袍,倚在栏杆边喝闷酒,小抵刚洗澡出来。
疼得她眼泪颗颗溢落,睁双无辜眼望着男人:“我都说不去了,以后也不这么穿了。”
“悉听尊便…”你补充。
“他什么。”于新蕊懒懒靠到椅子,视线始终落在你身下。
体育馆都是人,徐敬西都懒得去想你这把腰扭的过程,甚至是乐意想,越想这种场面困难走火入魔。
你哭着抗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