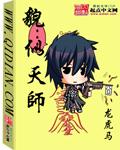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现实主义题材是什么 > 第110章 张辽(第1页)
第110章 张辽(第1页)
五四假期过去两天,我已经要闲出个蛋来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捧着手机却不知道该干嘛。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胡乱抓了把头发。
“好无聊啊!”我发声大喊。
罢了罢了,还是出去走走,透透气,一直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人流如水,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沥青路。
骄阳正好,有孩童一前一后,追逐打闹,欢笑不断,我却仍低着头,周遭的环境与我本就无关。
抬起头,我看见远方高处有一棵高大的参天松树,我便知道,那是东江河畔边的那棵树。
反正闲来无事,过去走走,也不是件坏事吧。
我步行将近半小时,移步换景,至树下。
阳光打在树叶上,透过间隙将石板路印的斑驳陆离,老树垂髫着屡缕藤丝,树下的石板凳也因岁月的磨砺而变得十分陈旧。
我抹了一把灰,随意坐上板凳。
远方东江河涟漪不断,河畔边有不少垂钓者,但大多沉默着,谁也没有理会谁。
我不禁想,要是几十年后我工作退休,是不是也会如他们一般,在每个清晨或夜晚,都带上钓具来到河边或海边一坐就是一天呢?
大概是不会的,因为我即使无事可做,也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
那么此时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身为一个高二的高中生,我想大概就是努力学习吧。但是我却无法静下心来了。
纵使有人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我也不会因此而焦虑,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虚学与不学,在于自我,又怎能关乎他人。
我摆动着双腿,踢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埃,看着他们漂浮又落下,如同我的青春一般,突然到达顶峰又突然落下深渊。
我站了起来,大抵是觉得无聊,准备回家继续躺着。
回眸处,我却一愣。
有人正站在斜坡之上,双手插兜,因为背负阳光,看不清脸,但可以得知,他正俯视下方的我,下颚微微扬起,颇有傲骨之气。
我眯了眯眼睛,还是看不清,那人似乎一直盯着我,他想必也发现了我正在盯着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挪开视线,只是依旧盯着我。
我被盯得发毛,准备从一旁的楼梯离开。
“喂!”那人喊道。
我停下脚步,继续斟酌那身影的身份。
那声音低沉又有些沙哑:“李贽吗?”
我愣了一下,回应道:“没错。”
岂料那人直接从斜坡滑了下来,然后稳稳站住,几步走到我的面前。
我这才看清他的相貌。
留着一头长发,打着唇钉和鼻钉,随着头发的漂浮,依稀看得见他一只耳朵打满了柳钉,穿着一身黑夹克,修身牛仔裤,加上优越的身高,显得有一股狂野之气。
这正是我那位已逝挚友的亲生哥哥,张辽。
印象中,他沉默寡言,烟不离手,喜欢摆弄吉他,常常与一些非主流地人在酒吧驻唱。
但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就再未见过他,听说他去了上海发展,还出了唱片,玩起了真正的摇滚。
“好久不见了,大概是……”张辽微微皱眉,掰起手指数起时间。
“四年。”我淡淡地说。
他拍了下脑门:“哦哦哦,对对,四年了,你这家伙也长高了不少嘛,就是表情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变得特别阴沉,反而让我第一眼没认出来呢。”
“嗯,话说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不是在上海发展吗?”
他撩了下右鬓的长发:“确实,我出了很多唱片,很多歌,在业界口碑也不错,所以最近又在筹备新歌,但实在没有灵感,公司就给我放了一个月假找找灵感,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于是就来了广东,一来到广东我就想起你这家伙,听了之前认识的人说你在光明读书,确实挺惊讶的,刚准备去你家找你,结果在这里遇到了,真是巧。”
张辽说话很具跳跃性,有时聊天能把人聊懵,但是这并不妨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