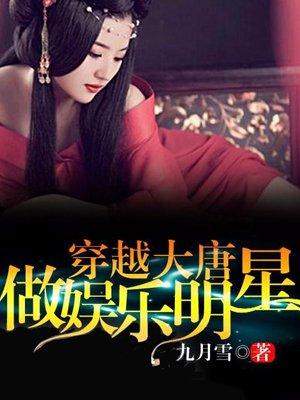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名门绅士泰剧在线观看 > 178 拔毛凤凰不如鸡不如自挂东南枝8(第4页)
178 拔毛凤凰不如鸡不如自挂东南枝8(第4页)
郁九九点头,“我知道了,谢谢你。”
郁九九曾有那么一丝奢望季天冉能认出她,可很遗憾,他看着她的脸,喊木星的名字,而看着每日轮班的护士说是郁九九。甚至连季封和练诗语也能搞错,有时能叫正确,有时又不认识他们,说话吐词口吃不清晰,得非常认真才能听明白他说什么。加之他身体不能轻易搬动,即便想带他到熟悉的环境里去走走看看都不行,练诗语和郁九九只能在床边每天趁着他醒来的时候与他说说话,希望他的情况能尽快好转。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刚好周六,刚过完十一假期,郁九九婉拒了朋友们为她举办生日party,十一假期她和他们见过面,就算是为她祝贺生日了。她二十八岁生日这天,陪在季天冉的病床边,他醒了,她跟他聊天,叫错名字也没关系,他叫错一次,她更正一次。他睡了,她就在旁边安静的看着书,等他下一次醒来。
手机被郁九九调成了无声,偶尔看了一眼便会发现收到很多生日祝福信息。合上书,郁九九发觉生活如她这般倒也不错,没有张扬放肆的性格,于是她避免掉很多麻烦。也没有沉默不语一字千金难开口的安静,让她不会被人误会太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班会老师让自我介绍,很多同学说到自己的性格,她记得自己说的话。
她最大的性格就是没有性格。
当时同学哄笑,其实她说了实话,她觉得自己就是没性格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弄出一个框架把自己框住,人怎么可能晓得几十年的未来生活会遇到什么事呢?总有事会改变人的性格和观念。有些人信誓旦旦的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不过是一个阶段,不要轻易说自己的性格是什么,也不要动不动就说了解谁,没人可以真正彻底的了解一个人,因为人的性格是变化的。小时候她自卑,不爱说话。妈妈不让她被欺负,又想她长得壮实点,报名参加散打兴趣班,渐渐的她变得强势霸道。之后到郁家,开始胆小,战战兢兢,说话不敢大声,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小包袱。可后来呢?哥哥疼爱,爸爸宠爱,她也有了大小姐脾气。
大部分的女人,当女儿的时候,是娇
俏可爱的。当女友的时候,是温柔任性的。变成妈妈之后,不理智娇弱都会被母爱的坚强和伟大改变,听说当了妈妈之后性格会变成很温柔,对世界包容也会宽广很多,对不切实际的东西会不再奢望。
放下书,郁九九轻轻的握住季天冉的手。
季天冉,我从来没主动牵过你的手,想不到第一牵你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是个好员工,好姐妹,但一定不是个好的女友。爱情,可以将就。也许,我的婚姻也可以试着将就。当你恢复了之后,我一定试着成为你合格的女友,跟你一起用心走向婚姻,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我再不会对你说,不要乱开玩笑,不会躲避你的亲吻,不会将你排斥,更不会再让你感觉到我随时都能和你分手。你很好,是我不够好。
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温柔相待,很可能没有机会再对他温柔。那些当初以为果断决绝的拒绝是最好最仁慈的言词,其实回头再看,她可能错了。因为,任何人都不该用‘直爽’这个词来为自己的残忍开脱,一句说出口的话,衡量它伤不伤人的标准不是你说话能说多狠,而是听话的人的承受能力。郁九九想,太过份的话,应该是没教养,而不叫直爽。
“季天冉,我以前对你说过最过份的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郁九九又想,她对他说过过份的话吗?最多的是让他不要喜欢她,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呵……”
郁九九轻笑,当初以为绝对不会在一起的人,居然会发展成这样,老天爷是最爱开玩笑的人。
“我当初说了那么多让你别追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呢?”
她是知道暗恋滋味的人,害怕被云长安拒绝,可她自己却无情的拒绝季天冉很多次,很多次。
郁九九一颗眼泪掉到了季天冉的手上。季天冉,快点好起来,我已经自省很多天了,等你恢复健康了,我会变成乖顺的女友陪着你。
*
国外,某饭店。
生日歌轻快的唱在房间里,蛋糕上的蜡烛微微晃动着火苗,穿过火苗的尖儿可以看到对面一张清俊非常的脸,平静的表情让人看不出他是今日的寿星。
“来来来,歌唱完了咱们吹蜡烛。”Maarten招呼云长安吹蜡烛,不想他动也不动,“你不吹?今天可是你生日哎。”
裴珮笑着看着云长安,“是啊,一口气吹灭蜡烛许的愿特别灵。”
云长安这才欠起了一点身体,把蜡烛吹灭,默然无语。
“许愿了吗?”Maarten问。
看着大蛋糕,云长安轻声道,“你们切吧。”
“裴珮,来,你切。他忒不好玩了,自己生日这么不上心。”
原本Maarten打算为云长安举办一个好玩的生日趴,没想到才提出来就被他否定了,他只愿意跟他一起吃个饭,这还是在他提醒他过生日的前提下才决定的,若是没人告诉他,他连今天是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Maarten和前一天飞来的裴珮为云长安切蛋糕,两人有说有笑,等蛋糕切好了之后,裴珮抬头,看到云长安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手上一根香烟在慢慢的燃着。他心里有事难抒的时候,就会抽烟。裴珮想走过去,Maarten拉住她。
“吃蛋糕吧。”
裴珮再看了云长安的背影一眼,他很少抽烟,如果她没记错,去年的生日,他也抽烟了。他不说,Maarten也不说,可不代表她想不到,在国内的某个女孩也是今天生日。她比他整整小三岁,他被人称九少爷,而她被人喊九小姐。
裴珮低声问,“又想她了吗?”
Maarten耸耸肩,谁知道呢。
“当年分手不是分得很干净吗,都两年了,还不能忘记呀?”
“不知道。”
裴珮小声的嘀咕,“我倒没看出来他对那个女孩有多深的感情。”若是喜欢,分手做什么,她可没逼他。他也不是别人逼他,他就听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