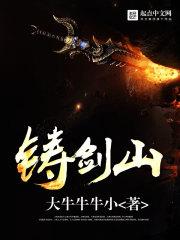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穿越清宫排行榜 > 第103章(第1页)
第103章(第1页)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以“操守清廉”著称的江苏巡抚张伯行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两件事的发生,使他对张元隆集团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其一是康熙四十九年六七月间张元隆的商船连续遭遇海盗抢劫,引起了张伯行的高度重视。[3]张伯行从中发现了张元隆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的现象,从而大体摸清了张元隆及其船队的概况。其二发生在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据张伯行两年之后的回忆称:“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带领官兵搜缉海贼郑尽心等,臣即专差赍咨驰赴江宁与督臣(噶礼)会商。据该差回称,督臣于十二日已往镇江,坐艍犁船出海矣。臣标并无战船水师,正与本标将弁酌议作何速往搜缉,又闻督臣从镇江由运河来苏,臣遂出郊远迎。十六日督臣到苏,臣问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入海,则尽山水花鸟,一帆可达;若由上海出口,实属迂远。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开行,臣亦于是日带领官兵随往……于十九日早同抵上邑(上海),提臣(师)懿德亦即继至。据提臣云,接到部文即委苏(州)、狼(山)二镇总兵出海……督臣又将(狼山镇)穆总兵差人赶回。臣与提臣俱不解其何故。”[4]
带着疑惑与不安,政治使命感极强的张伯行多方访查,大海商背后的谜底终于浮出水面——“访闻四十九年九月间(张)元隆闻郑尽心等在奉天败走,恐致破露,即使伊弟张令涛夤入督臣内幕,多将洋货贿赂。其督臣在上海时,十数船所铺设者,皆元隆所馈也。伊弟张令涛押船护送至宁波入口,远赴江宁。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镇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宁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余。铺设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缉贼之名伪装运货贿计耳”[5]。
在张伯行的题本中,“恐致破露”作何解释?张元隆重金贿赂噶礼意欲何为?康熙朝的奏折和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江南提督师懿德具折谢罪,罪名是用水师战船运米。[6]用战船运米是有先例的。康熙四十九年秋,福建漳、泉等地歉收,朝廷特谕“截留江南、浙江漕米三十万石,令福建提督、总兵官以战船运往赈济”[7]。每年例行的漕运多有波折,使用战船护送亦当在情理之中。看来师懿德的“运米战船案”一定与赈灾和漕运无关。康熙五十三年三月甲辰,“兵部覆,江苏巡抚张伯行疏言:商船、渔船与盗船一并在洋行走,难于识辨,以致盗氛未靖,商船被害,嗣后请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官兵易于稽查。至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俱应如所请,从之”[8]。此前,张伯行曾以相同内容密奏康熙,并指出时下“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营船可以为民船,民船亦可以为营船”,康熙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9]张伯行船制改革的建议,实出于“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的现实。这一现实使战船伪装成民船成为可能。此外,张伯行强烈要求“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张伯行还曾经具疏指出,“张元隆伙贼甚多,将苏州米粮买去”[10],可知张元隆与贩卖稻米出洋直接相关。于是,尽管史料证据还不充分,但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张元隆案”(即“大海商风波”的缘起)的轮廓:张元隆的海上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大量私贩米谷。而其旗下船只可能不敷使用,于是行贿噶礼,借用战船伪装成民船运米。同时,张伯行还发现“有船有人有票而船册无名种种,弊端不一,于是乃知张元隆代领照票,不止华亭一邑也”[11]。这使张伯行对张元隆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他心目中的张元隆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经营大宗稻米走私的大海商,与海贼郑尽心无异。同时他认为,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海上集团的走私活动,按律应当严惩。由于康熙朝部分奏折的散失,张伯行将张元隆案以及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一事密奏康熙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清,但在督抚互参案过程中,噶礼曾经辩白道:“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12]由此可以推断出张伯行可能应在康熙四十九年年底已将此事密奏皇帝。张伯行密奏张元隆出洋贩米之事,参劾噶礼受贿、包庇,把“大海商风波”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由于张伯行密奏之折的散佚,使我们无从知晓康熙的最初反应。但是很显然,康熙五十一年的江南盗匪案、江南科场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督抚互参案事关朝廷体面与政局稳定,影响太大,使康熙无暇顾及江浙沿海的稻米走私与海上集团。恐怕在整个康熙五十一年里张元隆只不过是康熙眼中的一个海贼而已。
张伯行见康熙并未重视“张元隆案”,便继续自己调查。康熙五十年,张伯行开始在全省密拏张元隆。张元隆属下船主余元亨等人因照票不符,俱被盘获,供出“照票亦系张元隆代领给付”[13]。于是,他“饬令署上海县事,常州府通判周葑提究元隆”,然周葑详查后称:张元隆已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死。[14]已经在押的海贼郑尽心又声称自己不认识张元隆,这使“张元隆案”几乎成了死案。然而,张伯行不甘心就此完结,他发现“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于是对张元隆的死讯顿起疑意,并下手令搜捕张元隆洋行的各船船主。不久,“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据房屋,谓其旧有噶礼幕客,今匿(江苏布政使)牟钦元署中,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15]。案情又起了新的波澜,似乎给了张伯行一个突破口。于是他命人到处捉拿张令涛,“数次令牟钦元交出……又令属员转告牟钦元交出”[16]。双方交涉多次,牟钦元始终不承认自己窝藏张令涛。事情一拖就是半年,张伯行突然将牟钦元的布政使大印收缴,并“派出官兵,将(布政使司)衙门四面包围,派道员二员,将内外尽行搜遍,并未拿获张令涛”[17]。派兵到藩司衙门捉拿嫌犯,张伯行本人也顶着很大压力。他向康熙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伊(牟钦元)乃传播谣言,说臣诬指平民张元隆、李崇御为海寇,又严拿张令涛,必欲置之死地。(伊)要烧臣衙门,又要刺杀了臣。”[18]赫寿也说张伯行“总危言,似目今即有海贼,又惧怕,过分防身”[19]。张伯行甚至希望康熙将牟钦元调升他省。于是,张伯行“因奏劾牟钦元,得旨,革牟钦元职,下总督赫寿察审”[20]。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赫寿上了一个折子说,经过再审,顾协一(赫寿的折子里称之为“郭学义”)承认其对张令涛“与海贼交结,分得海贼之处,俱系听人所言”。“又经数次审讯,并无公证”。并称“将牟钦元参劾看管后,张伯行遣员搜查,奴才又严行二司,将诉讼、认识张令涛之人带去,两次详查,然并无张令涛”。[21]“问张令涛之子张二供称,伊父已往湖广、福建”[22]。从而全面否定了张伯行对张令涛、牟钦元的指控。这样,官方舆论的矛头转而直指张伯行,认为他操守虽好,实则诬告无辜之人。康熙又命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到江南复审。张鹏翮在审理督抚互参案时就倾向噶礼一边,这次依然对张伯行不依不饶。“审事大人张鹏翮等审问抚臣张伯行有无海贼,张伯行回称原无海贼。大人即驳问既无海贼,则你明是欺诳皇上了。张伯行倔强如故,终不自认欺诳。大人自四月初十审起至十三日,连审数日,总无认罪口供”[23]。张鹏翮在审案过程中屡参张伯行“捏造无影之事,屡以海中有贼诳奏”[24]。张伯行也上疏康熙自我辩护道:“臣为绥靖海洋起见,急欲杜渐防微,张元隆虽报身故,而其多党众,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处处皆能领照。且张令涛之在藩幕……纵非通洋,亦系豪恶,臣为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