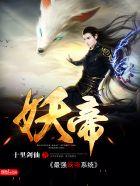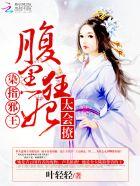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穿越清宫排行榜 > 第109章(第1页)
第109章(第1页)
当然,这是乾隆一厢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还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锁,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未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成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觐见乾隆,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对马戛尔尼的组成、使命、出发、航程,清政府的对策、接待、觐见、交涉以及使团的返回英国,作为极为详尽、细致的研究,把二百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使团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体会到由于谈判中止而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影响。当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其态度是积极而郑重的,派出了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其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七百余人,分乘五艘船支,经过十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清口外,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口。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对使团的食物免费供应,十分丰盛,并预先规定使团回国时将赏给可供一年食用的粮食。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写道:“在伙食的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异议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9]
这一切并不预示中英谈判将会顺利进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迥异,对这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理解也不同。中国方面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单纯的祝寿、观光,仰慕中华的声教文明;而英国的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
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是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葡伏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10]
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行三跪九叩礼毕”[11]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冰点。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根本没有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年过八十,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原字髻上部下加召)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12]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用重金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3]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14]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